最近,时代论再次成为了新闻焦点。有许多教导“被提”“敌基督已经兵临城下”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都是虚假的”(还有更多和末世相关的预言)的牧师们纷纷就 2023 年 10 月 7 日开始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是否已经被圣经预言了发表看法。这包括了罗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和格雷格·劳里(Greg Laurie)这样的知名大教会牧师,也包括了上百位不太知名的传道人。
在人们对中东问题兴趣高涨的时候,福音派的局外人(包括许多福音派信徒)会觉得,这种流行的对地缘政治的“圣经预言”就是福音派的共同观点。当然,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包括大多数知情的时代论基督徒)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神学对美国福音派的影响程度和局限性呢?
我最近出版了《时代论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Dispensationalism)一书,所以我应该对这个话题有资格发表一些看法。书名中的“衰”一词,乍一看似乎与最近流行的和讲坛上的末日论唠叨相矛盾。一些关键的定义和区别将帮助我们厘清已经多变的福音派神学中复杂和潜在的混乱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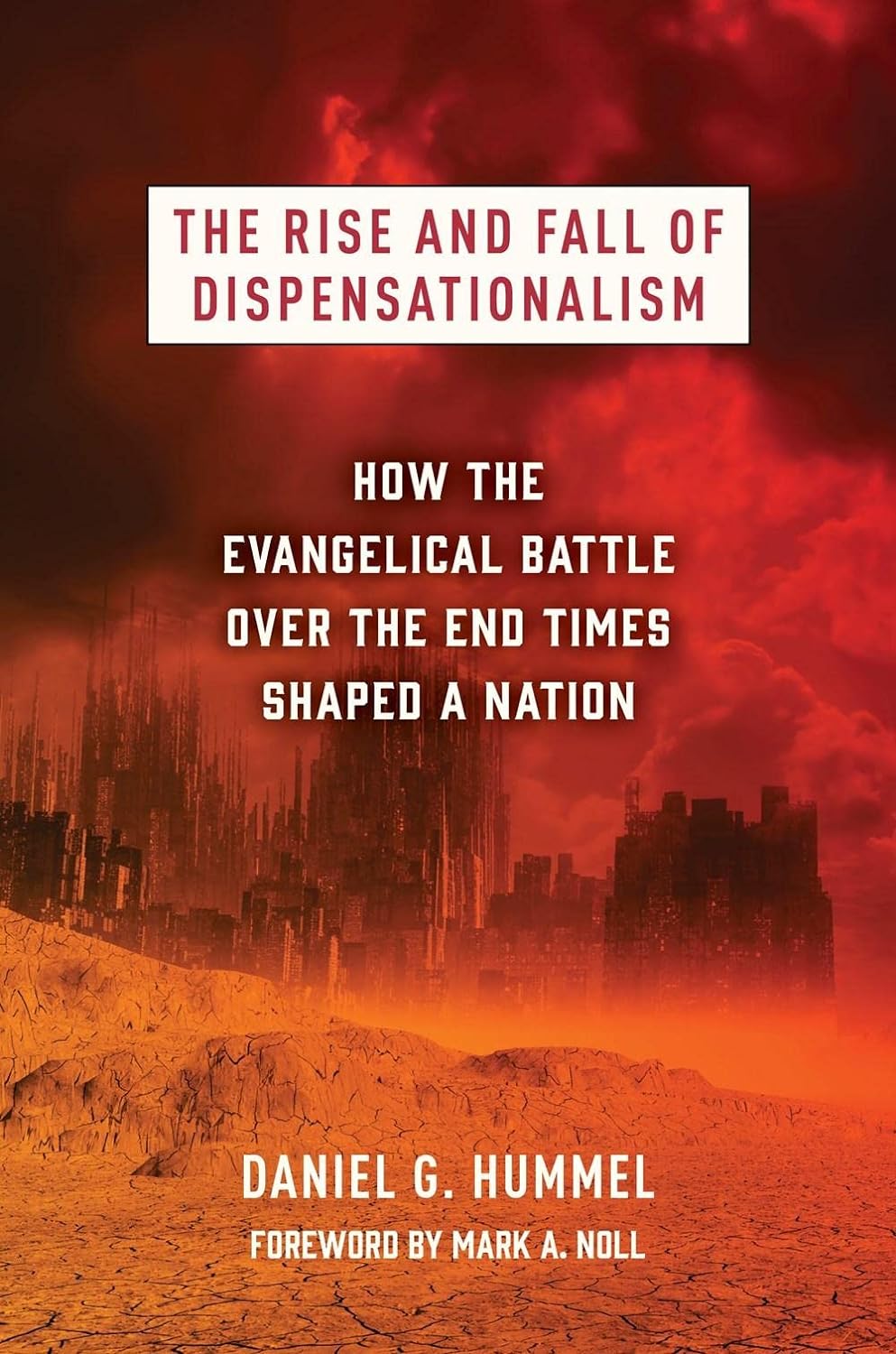 首先,尽管末世论神学最受关注(而且,无可否认,也是媒体报道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但时代论远不止是末世论。它是一个强大的神学体系,基于一套特定的解经方法,影响着基督徒对教会生活和社会中许多问题的态度。其独特的末世论拥有广泛的接受者,但它的其他核心教义也对解经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教会与以色列的区别以及神国的未来定位。
首先,尽管末世论神学最受关注(而且,无可否认,也是媒体报道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但时代论远不止是末世论。它是一个强大的神学体系,基于一套特定的解经方法,影响着基督徒对教会生活和社会中许多问题的态度。其独特的末世论拥有广泛的接受者,但它的其他核心教义也对解经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教会与以色列的区别以及神国的未来定位。
其次,今天的时代论有两大流派,这两个流派都值得讨论。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一是学术派时代论(scholarly dispensationalism),这一流派更多的是在一些神学院、基督教大学和少数教会中得到讨论和教导,但其在福音派中的支持者和影响力相对较小,相比前几代人而言我们可以说这一流派的影响力已经式微。
还有一个流派则是流行时代论(popular dispensationalism),其主要观点激发了书籍、电视、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体的灵感。一些教会——包括大型教会——以及福音派政治圈子尤其热衷于讨论这一流派。我们可以称之为“流行时代论”("pop-dispensationalism"),这也是大多数美国人最熟悉的版本,例如《末世迷踪》(Left Behind)系列小说和电影,以及类似于好莱坞喜剧电影《世界末日》(This is the End)中的末日神学。
当然,学术派时代论和流行时代论之间有重要的联系,但在风格、方法、可信度和实质内容上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区别,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时代论对美国福音派的影响。
查尔斯·瑞里(Charles Ryrie)的《今日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 Today,出版于 1965 年)主要讨论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术派时代论。基于这本书的形式,我们将对当下(2024 年)的时代论进行一次简短的概述。本文将简单描述学术派时代论与流行时代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在 1965 年的时候还不那么突出。
流行时代论继续在多种场合、通过多种形式的媒体为数百万基督徒的神学和属灵生活提供背景知识。以图书出版为例,美国亚马逊“基督教末世论”(Christian eschatology)这一子类型的畅销书排行榜显示,受时代论启发而对现代政治进行分析的著作高居榜首。大卫·耶利米(David Jeremiah)、阿米尔·察尔法提(Amir Tsarfati)和乔纳森·卡恩(Jonathan Cahn)的书经常名列前茅,托马斯·耐尔森(Thomas Nelson)、贝克(Baker)和丁道尔(Tyndale)等大型出版商也在出版此类书籍。
在其他媒体中,流行时代论仍然非常引人注目,有电视布道家(罗伯特·杰弗里斯和 2023 年去世的查尔斯·史丹利)和圣经广播(约翰·麦克阿瑟、查克·斯温道)等等。2023 年,《末世迷踪》系列电影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次的导演居然是凯文·索伯(Kevin Sorbo)。
值得反思的不仅是这些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还有其质量。在这方面,情况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愉快了。许多畅销书都是无休止的分析和预测,这可能会对读者产生扭曲的精神影响。
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前辈(如哈尔·林赛 [Hal Lindsey] 的《晚期伟大地球》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等书籍和《夜行神偷》 [A Thief in the Night] 等电影)一样,此类作品所呈现的末世论与时代论神学严重脱节。几十年来,许多深思熟虑的时代论神学家一直对此表示遗憾,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一滑坡潮流。
与它的前辈不同,今天的流行时代论也受到福音派文化和社会吸引力的高度拉扯。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代论人士声称要把福音信息传给非基督徒(虽然他们把大众对流行末世论的迷恋作为传福音的工具,但这是有问题的),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也取得了成功,但现在的流行时代论并没有试图扮演这一角色。它的产品针对的是现有的福音派信徒,并向他们推销自己的产品。
流行派时代论的问题在今天日趋严重,因为其商业化和受消费者驱动的发展进一步使其远离了学术派时代论。
即使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学术派时代论影响最盛的时候,这两者也曾出现过紧张关系,但尤其自那以后,它们就渐行渐远。这既是因为该教义受到了福音派神学和圣经研究学者中历史主义者越来越多的审视,也是因为许多曾对时代论深信不疑的机构抛弃了该神学。
虽然时代论在基要主义者或福音派中从来都不是唯一的神学传统(还有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无千禧年加尔文主义或乔治·埃尔登·赖德 [George Eldon Ladd] 的历史性前千禧年),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时代论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神学范式之一。它拥有一大批稳定的神学院和大学,以达拉斯(DTS)、泰尔博特(Talbot)和恩典(Grace)这三家分别位于美国三个不同地理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时代论神学院不断壮大,时代论知名神学家们也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奥斯瓦尔德·T. 艾利斯(Oswald T. Allis)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赖德(Ladd)等批评家开始,该教义的保守反对者在神学、圣经和知识方面不断提出并扩大批评。再加上从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到 N. T. 赖特(N. T. Wright)的英国批评家,以及近几十年来五旬宗和美南浸信会学术界对时代论的反驳,时代论在当今神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比上世纪任何时候都要小得多。
与此同时,这一神学曾经稳固的大本营也已经摆脱了历史上时代论对其的影响。像拜奥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这样离开时代论的例子在基督教神学院和大学界随处可见。拜奥拉大学由鲁本·A. 托雷(Reuben A. Torrey)和威廉·E. 布莱克斯通(William E. Blackstone)等时代论信徒于 1908 年创建,如今它所受的时代论影响已经很淡薄了,在某些地方甚至完全没有时代论的影子。
最近的另一个离开时代论的代表机构是穆特诺玛大学(Multnomah University),它曾是一所圣经学院,也是在其长期校长威拉德·奥尔德里奇(Willard Aldrich)领导下进行时代论神学研究和教育的中坚力量,现在被归入杰瑟普大学(Jessup University),成为后者的一个分校区。此外,一些宗派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美国播道会(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EFCA,曾是一个坚定的前千禧年主义和深受时代论影响的宗派)于 2019 年从其信仰声明中删除了“前千禧年”一词。
虽然如此,这一教义的“衰落”仍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包括迈克尔·弗拉赫(Michael Vlach)、迈克尔·J. 斯维格尔(Michael J. Svigel)和科里·马什(Cory Marsh)在内的时代论专业学者继续出版神学、圣经研究和历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帕特诺斯特出版社(Paternoster Press)和 SCS 出版社(SCS Press)等中小型出版社也在出版倡导时代论的书籍,学术派时代论学者参加了福音派神学协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ETS),并维持着自己的小型网络。
这两种发展——浅薄的、神学不足的流行时代论大肆流行和学术派时代论的衰落——是我所说的这一教义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衰落”的实质。然而,衰落既不是死亡,也不是消失。尽管今天它的影响有好有坏,但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至少在纸面上,仍有一些神学院和学校坚持这一神学。其中包括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和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它们是美国最大的两间培养牧师的跨宗派机构。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神学院,如南加州神学院(Southern California Seminary)、马斯特斯神学院(The Master's Seminary)和牧人神学院(Shepherd's Theological Seminary),也都致力于时代论特色,像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这样的本科院校也仍然在这一阵营中。
然而,具体观察每一间院校,我们不难发现学生们所接受和神学院所教导的时代论“浓度”不一。有的机构很明确肯定时代论,有的机构含糊其辞,有的甚至只字不提。此外,时代论的主张者承认很难得到主流学术出版商和学术期刊的关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学术性时代论在高等教育内外的影响力。
近几十年来,组织和扩大福音派事工中规模最大、最具新闻价值的运动中,明显时代论是缺席的。不仅如此,许多运动还对时代论充满敌意。当然,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些运动在与福音派历史性神学有着各不相同的连续性,但它们都是当今的重要运动,它们揭示了福音派世界的组织能量集中在哪里。
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新兴教会运动(Emergent Church)、“年轻、躁动的改革宗”“第三条道路”("Third Way",专注于传福音、社会正义和社区参与——译注)、基督教国族主义、红字基督徒(Red Letter Christians,强调遵从耶稣关于社会正义的教导——译注)等等,都对时代论神学提出了批评——而且理由各不相同。与 70 年前相比,当时的全球宣教运动、青年和大学事工运动,以及(几十年后的)耶稣子民运动和弥赛亚犹太教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时代论及其神学的推动。
或许,在福音派更广泛的群体中,时代论仍然具有领导地位的一个领域就是捍卫圣灵恩赐终止论(cessationist)观点。麦克阿瑟和贾斯汀·彼得斯(Justin Peters)这两位信徒在这方面很受欢迎。但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这一神学立场正受到来自五旬宗和非五旬宗基督徒越来越大的压力。
综合来看,这些轨迹表明,在美国福音派中,时代论的发展势头正在衰退,尽管这种衰退的原因极其复杂。
虽然流行时代论在商业和消费领域的成功令人惊叹,但它过去的一个关键影响领域却在减弱:受到教会支持的政治家。
20 世纪 20 年代,威廉·贝尔·莱利(William Bell Riley)和 J. 弗兰克·诺里斯(J. Frank Norris)等人向进化论和酒精发起了战争。20 世纪 50 年代,约翰·赖斯(John R. Rice)、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和J. 弗农·麦基(J. Vernon McGee)拥有全国最大的批评共产主义的平台。20 世纪 80 年代,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和蒂姆·莱希(Tim LaHaye)带头反对世俗人文主义。这些人都相信或非常认同时代论。
今天,虽然仍有著名的时代论牧师参与政治(杰弗里斯和约翰·哈吉,或约翰·麦克阿瑟对新冠政策的批评),但保守福音派政治的重心已转向其他方向。20 世纪 80 年代,对这一教义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是新近大肆鼓吹的后千禧年“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如今,这种“重建主义”在日益壮大的后千禧年国族主义者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道格·威尔逊(Doug Wilson)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本人早年曾是一位时代论者。他从这一神学中“转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所代表的保守改革宗后千禧年主义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发展是更大神学趋势的标志。
与改革宗后千禧年主义相比,美国基督教政治领域受五旬宗影响更具现实意义。宝拉·怀特(Paula White)等人曾担任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顾问,而哈吉(Hagee)则管理着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宣传团体——基督徒团结支持以色列组织(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
哈吉将一种改良后的末世论(他出版了大量流行末世论书籍)与五旬宗和成功神学结合,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混合体,吸引着不同的支持者和不同动机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哈吉的影响使他成为美国与全球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网络沟通的桥梁,而全球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网络绝大多数是五旬宗和成功神学人士(尤其注重《创世记》12:3),并在神学上的关键部分反对时代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当今国际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在实质和言辞上都反对时代论这一教义。
怀特则更接近于统治神学的立场,呼吁基督徒在社会和文化中行使权力。就政治议题而言,这一观点——以及全球五旬宗和灵恩派“网络”基督教的观点——更多地与保守的改革宗后千禧年主义相一致,而不是与时代论一致,如今,它为福音派政治组织提供了大量能量。
上述四点描绘出了当今时代论的复杂图景,横跨学术、文化和政治领域。我们无从知晓这一教义在未来50年中究竟会如何发展,但如果它确实在福音派神学院中重获影响力,或抓住了Z世代福音派信徒的想象力,那将是对当前趋势的显著逆转。
与此同时,如果时代论失去商业吸引力,这也会成为新闻,而且很可能标志着福音派文化发生了更广泛的巨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福音派文化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末世论正在淡化和逝去。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4 Snapshots of Dispensationalism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