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给我们带来的遗产非常复杂。许多人称赞他是历史和神学上的英雄——德国改教家,把钉子钉在了靠行为称义的心上。另一些人则抨击他是一个刻薄、自大的反犹主义者。还有人认为路德是人文主义者中的人文主义者,像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叛逆青年,把个人自由和理性从天主教教条主义的冰冷魔掌中解放出来。
这些批评和赞誉贯穿于宗教改革五百多年来的历史中,传奇的事实或虚构彼此之间互相拉锯,不同理念的主张者都提出论据把路德作为自己的英雄或者仇敌——这些人包括纳粹分子、福音派美南浸信会、自由派历史学家等等。但在阅读了两部令人愉快的思想史作品(蒂莫西·乔治的《改教家的神学思想》和迈克尔·里夫斯的《不灭的火焰》)之后,我意识到路德和他的改教伙伴们如何改变了教会历史的进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告诉你宗教改革给教会带来改变的四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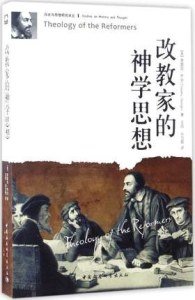 “要么行善,要么被诅咒”——这句话是天主教会的名片,它谴责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在宗教改革开始之前,16世纪的教堂仪式是一项无意识的苦差事,是一项政治要求,目的是为了获得神职人员水龙头里滴下的任何恩典。弥撒是用拉丁语进行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无法理解,是一种喃喃自语;而圣餐仪式是一个人的表演——神父从事的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形而上学的胡闹:把面包变成肉,把酒变成血,并希望借此“造就”所有人。
“要么行善,要么被诅咒”——这句话是天主教会的名片,它谴责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在宗教改革开始之前,16世纪的教堂仪式是一项无意识的苦差事,是一项政治要求,目的是为了获得神职人员水龙头里滴下的任何恩典。弥撒是用拉丁语进行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无法理解,是一种喃喃自语;而圣餐仪式是一个人的表演——神父从事的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形而上学的胡闹:把面包变成肉,把酒变成血,并希望借此“造就”所有人。
路德、茨温利和他们之后的改教家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问题。他们指出圣经所说的称义是一个一次性的、不可改变的宣告性判决,其依据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人在恩典中作出的拣选。改教家指出,基督徒所得到的“归算之义”完全是透过信靠基督在髑髅地完成的工作而获得的。这种理解颠覆了天主教会及其“渐进式”、一点一点增加善行的称义观。
路德更加完备的救恩论还在后面,经过了对圣经的深入研究。换句话说,“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必然结果是“唯独信心”(sola fide),这对于理解宗教改革神学的主旨至关重要。
茨温利得出了类似的观念,并且根据他自己的表述,他没有受到路德著作的任何直接影响。1519年1月1日,仍是罗马天主教牧师的茨温利摒弃了传统的拉丁文教会礼仪,开始用他的母语就《新约》开始解经式讲道。
1525年,茨温利讲完了整本新约,然后转而就旧约展开讲道。在此期间,茨温利与天主教会脱离关系、谴责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并在苏黎世废除了弥撒,使苏黎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新教国家。同时,路德为他的会众将《圣经》翻译成德语,并在1534年之前出版了德语《旧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上帝的话语以一种他们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能够回应的方式传递给人们。
这些行动改变了欧洲教会的面貌,为我们所知的新教铺平了道路。基督徒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智识和其他方面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以前,教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架构,所有这些突破为教会论的普遍转变打开了大门。
宗教改革还恢复了圣经中关于“牧师”或“神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论述。不明就里走过场的日子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再担任“中保”角色的牧师。现在,牧师的任务是将会众的心带到定睛耶稣基督上,基督是圣洁的上帝和有罪的人之间唯一的中保。
宗教改革后,忠心的牧师们不再试图以任何方式“注入恩典”或“实现救赎”,他们只是注视十字架和基于十字架的所有天国祝福。他们不再是恩典的泉源,而是成为把我们指向上帝的子民在基督里所拥有无尽宝藏的箭头。
然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把双刃剑,这把剑带来积极的改变,但也使得许多人在神面前没有能够聆听忏悔的“中保”了。如果牧师不听我们的忏悔,谁来听呢?宗教改革强调,每个基督徒的处境确实很糟糕;以前,这可能被敬虔的行为和圣礼的“戏法”所掩盖,但现在它就在眼前。人们开始对路德的怀疑产生共鸣。
 这一转变是如何实现的?最明显的是,宗教改革改变了圣礼——洗礼和主餐。婴儿洗是天主教会毋庸置疑的主要圣礼之一,但这也是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基本上都持有的神学信念。在其他地方都有相当大的分歧的情况下,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他们如此相似?
这一转变是如何实现的?最明显的是,宗教改革改变了圣礼——洗礼和主餐。婴儿洗是天主教会毋庸置疑的主要圣礼之一,但这也是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基本上都持有的神学信念。在其他地方都有相当大的分歧的情况下,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他们如此相似?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无数个层级。但鉴于并非所有的改教家都坚持婴儿洗——例如,门诺·西门和重洗派就反对婴儿洗,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大胆猜测。
这里有一个可能的原因:路德、加尔文和其他人根本无法设想一个独立于国家的教会。教会与政治的关联太深,以至于路德把教会称为“上帝的右手”,把国家称为“上帝的左手”。虽然西门和分离主义的重洗派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洗礼脱离了教会,但他们更接近于今天信而受洗主张者对洗礼的理解。因此,尽管宗教改革并没有普遍接受信而受洗观,但它提供了恢复这一教义的框架。
在整个宗教改革中,很少有像主餐教义那样引起分歧的。虽然改教家们脱离了罗马,但他们也彼此冲突。
例如,路德强烈谴责变体说是一种形而上的神秘主义,但却主张一种被称为“同质”(consubstantiation)的神学半路凉亭,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质与外表的区别。根据路德的观点,在圣餐中,基督存在于饼和酒之中、之下(in, with and under),当我们领受饼和酒时,字面上(literally)我们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加尔文认为路德和天主教的观点都站不住脚。他肯定了所谓的“属灵临在”,即在主餐期间,基督是临在的,但这种临在是属灵的,“只有真信徒透过信心才领受了基督”(《基督教要义》4.17.33)。
茨温利更进一步,主张一种“纪念”的观点,即在吃饼喝杯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只是宣扬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直到祂再来,同时同享祂带来的益处。
路德冷笑道,茨温利的观点是对神的亵渎。否认基督在其晚餐中的身体同在,就是否认基督的无所不在。这种分歧在1529年10月达到了顶峰,当时路德和茨温利在黑森亲王腓力(Phillip of Hesse)授意下会面,试图建立一个泛新教联盟来对抗教皇和他的军事力量。不出所料,两人无法忽视他们在这一点上的分歧,联盟也就没有诞生。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神学争论似乎是近视的。面对如此迫在眉睫的利害关系,这两位新教神学家难道不能放弃神学上的细枝末节,建立某种同盟吗?不幸的是,不能。
尽管如此,宗教改革对主餐的重新定义仍然产生了压倒性的积极效果。虽然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有一个真理仍然是不可改变的:圣餐并不赐下恩典——这一能力来自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关于圣经中的另一个圣礼——洗礼,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随着西门和重洗派的出现,信而受洗的教义基础已经得到建立。哪怕是仍保留婴儿洗礼的宗派也不再赞同天主教的婴儿洗礼观,后者主张婴儿洗礼能赐下恩典、具有救赎性。没有人仅仅因为出生而获得属灵的特权。
同时,也没有人拥有任何特权,因为宗教改革清楚地表明:各各他的地面是平的。在那里流的血是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反犹主义者和福音派美南浸信会、德国人和法国人、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和第一年的神学院学生而流的,所有不义的人都需要救主的义归算给他。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4 Ways the Reformation Changed the Chu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