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过去几十年间,越来越多人认可并称赞同理心(empathy)为一种美德,很多人甚至认为同理心优于同情心(sympathy)。因为同情心使安慰者和受苦者之间仍保有一定距离,而同理心则令安慰者更深地进入受苦者的痛苦中。然而,若我们对由同理心形成的情绪和关系动态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它对安慰者、受苦者、甚至对领袖、教会和整个社会存在一些潜在危险。在一段关系中,同情心保持着更多情绪空间,但也许我们正需要这个空间距离,才能为受伤者带来真实有效的安慰。
如果查考不同英文译本的希伯来书4:15 ,你会发现大多版本使用了体恤(sympathize)这个词来描述大祭司对我们软弱的态度。和合本写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NASB、NKJV、CSB和NET版本均采用了这个词。
然而,英文新国际译本(NIV)则采用了“同理”(empathize)这个词,读起来是这样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同理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我们讨论的这个英文单词对应的希腊文是sympathizo。尽管它的英文同根词应为同情(sympathize),但英文新国际译本采用了一个不同的英文单词 —— 同理(empathize) —— 来翻译这个希腊单词。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化,这两个英语单词只是前缀不同。体恤(sympathy, 对应的拉丁文为compassion,即同情)一词的字面意思为“与……一同受苦”(希腊文为sym+pathos ;拉丁文为com+passio)。而同理(Empathy)一词意为“在……中受苦”。
英文新国际译本版本选择的单词,反应了从同情到同理的更广泛文化挪移。 然而,从“与……一同”到“在……中”这个转变重要吗?在去年的数篇文章中,我都表示肯定,甚至会提到“同理心之罪”。[1] 我理解这样说可能令一些读者感到惊讶。同理心岂不是一项美德吗?既是这样,何来“同理心之罪”?
本文尝试阐明同理心的价值和危险,以及在当今社会中,它与同情心之间的关系。
同理心(empathy)作为一个术语是近些年才出现的。[2]这个词在二十世纪从美学领域进入英语世界。它的原意是“感同身受”(feeling in),指的是将自己想象中的感受投射现实上的能力(这个定义几乎与它的当代含义背道而驰)。1955年,《读者文摘》将这一术语定义为 “欣赏他人的感受却不因情绪而影响自己判断力的能力”。
“同理”一词如果直译的话,是 “感同身受”的意思。最近在《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作为社会和个人心理学范畴的理念,我们很难评估同理心成功与否。[3]简单而言,这个词没有公认的定义,以致人们几乎不可能对它进行分析和评估。作者在本文中列出了一些可能的定义:
换言之,同理心有时被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认知行为。这是一种从他人角度出发观察事物的能力,去真正地理解他人思考的内容和方式。 一个富有同理心的人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同理心的认知理解有时被称为“观点取替”。
而另一方面,同理心有时是指一种情感或情绪行为,不仅是知道别人的感受,更是能实际地感受到他们的感受(经常被称作“共情”)。如果他人开心,我就开心;如果他人悲伤,我就悲伤。
又或者,同理心也可能不是指分担他人同样的情绪,而是指我们给予受苦者的温暖感受(根据这一定义,同理心有时等同于怜悯心或同情心)。 有时这种“感同身受”是自愿的;我们选择将自己沉浸在他人的感受中。 有时,这是非自愿的;富有同理心的人,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愿意,都对他人的情绪高度敏感并被之左右。
有时,同理心是作为同情心和怜悯心的近义词来使用的。尽管如此,在当代的许多讨论中,相较于同情心,同理心被认为是提供安慰和帮助的更优越方式。
例如,布琳·布朗(Brené Brown)坚持认为同情心使人互相疏远。[4]因为同情心超脱于痛苦之外。它总是试图在他人的痛苦中找到一线希望。而同理心则促进人际情感联系,在痛苦的黑暗中加入受苦者,并不作任何论断。有趣的是,布朗将同理心定义为“与他人一起感受”( "feeling with people"),而不是“与他人感同身受”("feeling in people")。
对布朗而言, 同理心和同情心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了不对称性 —— 一位受苦者和一位安慰者,一位陷入痛苦泥沼的人及另一位想去帮助他的人。然而, 同理心试图将这种不对称感降至最低,既不对受苦者进行评判,也不对他们绝望的言语作出急切的回应。相反,我们只是与受苦者一同坐在黑暗中聆听。
根据以上对同理心的定义,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理心这一概念中的许多值得赞许之处。 尝试理解别人、换位思考 、辨识他人的真实感受,这都是好的。与他人有同样的感受也很好——“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罗12:15)。对身陷苦楚之人给予温暖和怜恤的情感更是美好(受感动之余,希望可以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
 无论如何,魔鬼喜爱在无辜的词汇中,尤其是美德相关的词汇里,隐藏真实的罪。比如,在当代的宽容思想下,同理心的概念可以隐藏无数有害和罪恶的互动。[5]词典对它的定义是一回事,打着同理心大旗的情绪和现实中的关系互动才是真实的问题。[6]甚至我认为将同理心代替同情心作为首要的美德,在此引用C. S. 路易斯的一个说法,“不仅仅是语言学的意义了。”[7]因此,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批判性地评估同情心到同理心的转移。
无论如何,魔鬼喜爱在无辜的词汇中,尤其是美德相关的词汇里,隐藏真实的罪。比如,在当代的宽容思想下,同理心的概念可以隐藏无数有害和罪恶的互动。[5]词典对它的定义是一回事,打着同理心大旗的情绪和现实中的关系互动才是真实的问题。[6]甚至我认为将同理心代替同情心作为首要的美德,在此引用C. S. 路易斯的一个说法,“不仅仅是语言学的意义了。”[7]因此,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批判性地评估同情心到同理心的转移。
如本文之前提到,体恤(Sympathy)这个英文单词直接来源于它的希腊文sympathizo。它对应的拉丁文为同情(compassion),意为“与……一同受苦”(希腊文为sym+pathos ;拉丁文为com+passio)。那么,作为具有重大转变意义的第一个线索,我们会问:“说我们应该与他人一同受苦,和说我们应该在他人痛苦中感同身受,这两者有何不同?”
两种说法都以受苦者为方向,但他们有不同的呈现。同情心指的是心甘情愿地加入受苦者的苦难,同理心则指的是全面地使他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的痛苦。实际上,这也正是为何有人认为同理心是对他人痛苦更有爱的回应。与他人一同受苦,看上去是在安慰者和受苦者之间维持着一定距离的情感分隔或界限。“同情心”强调的是:我和他一起,但我不在他的情绪里,我们保留自己的个体整体性和界限;我仍旧是我,你依然是你。
对于有些作者来说,同情心产生的情感距离正是同理心已经克服的问题。同理心鼓励我的情感和受苦者的情感更充分、更完整地融合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同理心的美德(以及它较同情心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它使人更充分地沉浸在他人的痛苦和感受中,通过进入他们的经历而完全地感同身受。 就如布朗争辩的, 同情心维持了安慰者和受苦者之间的不对称性,而同理心则试图通过不加判断和评价来减少这种不对称性。
此刻,我们需要留意到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情心产生的情绪界限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可能假装同情,其实是冷漠的,没有分担苦难、疼痛或情绪,也没有与哀哭的人同哭。
当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时,我们爱受苦者的方式,要么通过在他们的苦难中改变他们的神学观念,要么挥舞着圣经真理去纠正而不是安慰他们。我们笨拙地提出纠正,然而受苦者可能最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而真心的认同,认同他们的痛苦是真实和深刻的。或者,他们也许不需要任何的话语,最需要的只是陪伴和眼泪。当我们发现别人的压力和痛苦令人不安时,便试图叫停以回避这种痛苦,违背受苦者意愿并迫使他们离开苦境。这才是真正的危险。[8]
然而,同情心和怜悯心隐含的情绪界限和情感分隔可能还有另一个目的。它们可能使安慰者保持必要的稳定性和自我差异,以向受苦者提供他们所需的真实安慰和帮助。例如,阿拉斯泰尔·罗伯茨(Alastair Roberts)以这种方式区分了同理心和同情心:通常来说,同理心从根本上或主要以受难者的感受为导向;同情心(或称怜悯心)则从根本上或主要以他们的益处为导向。[9]
由于同理心(在某种定义下)是一种与受苦者的即时感受紧密相连的情感联系,它可能更倾向于产生被动反应。同理心令人试图迅速缓解貌似最明显的痛苦来源(因此有时我们会把症状误认为是根源)。而另一方面,同情心,由于是从根本上关注受苦者的整体益处,则更多地是主动回应(responsive)而不是被动反应(reactive),因此人能够冷静思考、慎重行事,以应对他人的痛苦。
然而,为了拥有这个稳定的回应态度,同情心必须拥有一个情绪空间,以考虑整体的情况,且不至于迷失于眼前的痛苦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情心和怜悯心涉及的 “分隔”不是来源于冷漠,而是来自对受难者得益处的深切渴望。更重要的是,同情心是谦卑的,因为它认识到,当下的火热情绪可能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火热的情绪可能模糊了我们对最需要的东西的看法。
因此,如果同理心意味着暂停判断和更全面地共情,那么它的危险就是在另一个人的疼痛和苦楚中的沉浸。如果受苦者在流沙中沉沦,一位有同理心的帮助者可能试图双脚跳进去流沙中。而一位有同情心的帮助者则会一只脚踏入流沙,另一只脚牢牢踩在岸上(这就是情绪界限)。 同情心会抓住外面坚固的东西作为锚,以便更好地帮助陷入流沙中的人。即使是布琳·布朗在赞扬同理心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这种危险。[10]
假设在深洞内挣扎,同理心不是跳进洞内和他人一起挣扎,体会他人的情感,或者把他的挣扎当作自己的挣扎来解决。如果他的问题变成了你的,那么现在则是有两个人同时落在洞里了。这根本帮不上忙。因此在这里,界限很重要。我们若真想带着同理心出现,则必须知道我们在何处止步,他人在何处开始。
这种危险,对于天生就有很强同理心以及对他人情感高度敏感的人来说,尤为严重,因为他们容易被他人的悲伤和愁苦所吞噬。对他们而言,界限尤为重要,不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或是向他们求助之人的益处。
然而,同理心的危险范围不仅仅只触及涉及到个人。同理心也会对社会群体比如家庭、教会、机构甚至整个社会都带来重大挑战。
埃德温·弗里德曼(Edwin Friedman)是一位拉比和家庭治疗师。他在所著的《神经的失败:快速修复时代的领导力》(A Failure of Nerve)一书中提出警告:将同理心提升为领袖的首要美德是危险的。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尽管领袖们需要感受、关心、认同、回应他人并分担他人的痛苦, 但在现代背景下,同理心往往是“焦虑的伪装……是敏感者手中的权力工具。”[11]
为何同理心在现代社会如此突出?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因为“一个焦虑的社会所特有的群居/团结力量”。这种社会允许社区中最不成熟 、最具侵略性和反应最大的成员通过要求其他成员适应他们及他们的敏感度,来胁迫社会议程。[12]对于弗里德曼而言,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关心受伤者;他毕竟是一位婚姻和家庭咨询师。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允许反应最大和最不成熟的那些成员的敏感度和关注点,来设定家庭、教会和机构的议程。(阿拉斯泰尔·罗伯茨很好地总结了弗里德曼的观察。[13])
当同理心被认定为一种(或唯一一种)重要美德时(尤其对领袖而言),它会带来特别大的破坏力和挟持威胁力。正如C.S.路易斯在《梦幻巴士》中写道:“过度的怜悯之情(或称同理心)或者说我们遭受的怜悯之苦,导致人们妥协于不该让步的东西,在该说真话的时候却阿谀奉承。”[14]在同理心的影响下,我们可能将自己暴露在约翰·派博说的“情绪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中。
当一个人将他自己的情感痛苦归咎于对方不爱他时,就会产生情绪勒索。但这两者并不相同。 一个人可能深爱对方,但被爱的一方仍然觉得受伤,并以此勒索爱人去承认一些不存在的罪疚。情绪勒索者会说:“如果我觉得你伤害了我,你就是有罪的。”不容任何辩护,受伤者已经变成了上帝。他的情绪就是法官和陪审团。真理不再重要。最重要的只是受伤者的主观感受、不容置疑。这样的情绪手段是一种大恶。在过去三十年的事工中,我经常看到这类事情发生,并迫切为那些被情绪勒索受冤屈的人辩护。[15]
当这些动态存在时,同理心通常导致胆怯,不愿意(哪怕用很笼统的方式)去指出任何可能给他人带来苦楚的事情(尤其对那些已经受伤的人)。出于善良而真诚的愿望,我们想要去保护受创伤和虐待的人,便保留不提某些话题和真理。有些话一定不能说 (要么说时注意层层包裹,使用各种限定条件、巧妙的用词和语调,以致失去了话语的力度),因为可能一旦说出口,便给受伤者带来更多苦楚。
这是因为,在同理心的控制下,我们无法区分他人的苦楚和对他人的伤害这两者。但想一想耶稣,当祂故意延迟出发去医治拉撒路时,这给玛利亚和玛大(还有拉撒路!)带来多大的苦楚!然而,使徒约翰形容这个延迟(明显带来了苦楚)却是爱的表现(约11:5-6)。
在同理心的影响下,我们很难区分苦楚和伤害。出于好意想避免伤害,我们承诺不说不做任何会带来苦楚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说出真理的能力在减弱和紧缩(有时是在高度同理人群的压力下),就如路易斯所言:“昔日悲伤作炼净之用,现今只能任其溃烂。”[16]
无论如何,为了避免我们误以为同理心只在面对真实的痛苦艰难时才会产生危险,我们不妨思想一下施虐者是如何操控受虐者的感受的:
“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一旦发现,我就麻烦大了。”这是对受害者同理心进行直接操控。(在讨论怜悯心之苦——也就是同理心——时,路易斯提到许多女性的贞洁因此被骗)。然而,操控并没有就此结束。 施虐者通常利用教会和社区的心软,以逃避对其行为应付的责任。 他们将人们对实际受害者的痛苦的关注转移到自己作为施暴者的痛苦上,期望我们对他们有情绪共情,阻止我们对应做什么进行理性的判断。
在类似案例中,教会缺乏的不一定是同理心,相反是同理心的彻底错位。但是为了确保我们的感情适当,我们需要保持适宜的情感界限,这样我们可以对当下处境进行清晰正确的思考。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同情心或怜悯心,因为它坚决主张自我分辨以及对长远利益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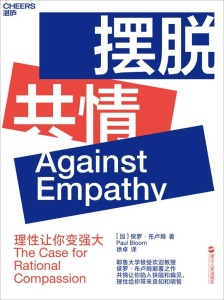 错位的同理心引起了一个最终的危害。耶鲁大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教授保罗·布卢姆 (Paul Bloom)写了一本书名叫《摆脱共情:理性让你更强大》(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17]
错位的同理心引起了一个最终的危害。耶鲁大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教授保罗·布卢姆 (Paul Bloom)写了一本书名叫《摆脱共情:理性让你更强大》(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17]
布卢姆提到,因为我们自身是有限的,只能感受到很有限一群人的感受,同理心则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因此,同理心仿如聚光灯,将我们与特定的人或群体(而不是其他人)的痛苦和感受联系在一起。这种同理的“近视”导致同理心争竞,一些人认同一个群体的痛苦,而另一些人认同另一个群体的痛苦。这种内在的偏见拦阻我们看清全局。我们努力保持适当的客观性。我们很容易把那些我们没与之同理共情的人妖魔化。因此,我们对内部群体的同理心,常常与我们对外部群体的强烈愤怒(甚至仇恨)相伴而行。因此,最近有一连串的文章指出,同理心的增强非但没有建立关系,似乎还加剧了两极分化和族群分裂。[18]
也就是说,我们的同理心经常带有选择性,将我们的对手变为恶魔,因为他们更容易令人憎恶。
最后,我主要关心的是这里描述的危险和动态,而不是标签。我不想拘泥于词汇。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完美而又正确地使用同理心一词。
这里举一个好的例子,亚比该·多兹(Abigail Dodds)很有力地说明了同理心的自然美善之处,同时也强调了它的重大危险。[19]更重要的是,她的文章强调了,对同理心适当位置的清晰认知,有助于男人和女人在家庭、教会和世界中一同服事。如果同理心单单意味着“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情感”,那么它不仅是好的,而且是爱别人所必需的。甚至某种情绪共情也是需要的,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以及保罗关于肢体的描述:“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6)从这个意义来说,同理心是一种爱的体现。
在辅导受苦者时,这点尤为重要。我的一位朋友是基督徒心理学家,他说:
对我来说,好的辅导——以神为中心的辅导——需要有共情的连接(不需要赞同他们的所有经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在自我意识中成长,以便基督能够进入他们未解决和未赎回的内心世界,从而带来医治。
这样看来,同理心并非优越于同情心,乃是同情心(怜悯心)的仆人。通过与受苦者共情(包括他们的消极和痛苦的情绪),我能建立关系和信任,跨过受苦者与其他人之间的那道鸿沟。 情绪连接的最终目的是将受苦者带到基督面前,使他得安慰和医治。同理心服务于同情心,同情心使我们采取爱的行动,就如在福音书中同情心常促使主耶稣帮助受苦之人一般(太9:36,14:14,15:32)。
同时,我自己喜欢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使用含有“与……一同受苦”之意的词 —— 表示同情或者怜悯 ——来指一种以基督为导向、以基督为纽带的推动力,与他人一同受苦、与他们感同身受、以及在不犯罪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认同受苦者。
当我们保持自己在基督里的基本身份和对基督的忠心时,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倾听他们的痛苦悲伤、同时考虑他们的即时感受以及最终益处,我们学习谦卑且有智慧地分辨他们感受到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并运用智慧使他们意识到这种区别。我们用自己的话语、眼泪、面部表情和陪伴与他们交流:“你的境况很艰难。我知道你很难过。我陪你一起度过,我们是有希望的。”
在这一切中,我主要关心的不是在受苦者痛苦的时刻纠正他们,也不是质疑受苦者深层次的苦恼。相反,我只是想坚持一个观点:安慰者在与他人一起分担痛苦的同时,要保持自己的正直。我们可以称之为维持界限、或保持自我分辨、避免陷入困境、拒绝败坏和不健康的同理心、抵制对感情这一偶像的崇拜、紧紧连接于真理和美善、保持对耶稣的忠诚。
无论你如何称呼它,它都绝不是完全沉浸在其他人的情绪中。它不允许其他人操纵我们的情感机制。在不该妥协处绝不妥协,真理绝不让位于社区中一个最不成熟和反应最大的成员的感受和敏感度。为了他人宝贵的生命,紧紧抓住耶稣,并有意识有智慧地进入他人的痛处。在他人的绝望中保持希望,明智地选择时机进行鼓励、劝诫和纠正。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对受伤者、伤心者和受苦者有深切的感受。毕竟我们蒙召要存“怜恤的心肠”(西3:12)。但我们的感受及我们与他人的共情必须紧系于真理、事实和基督。愿上帝帮助我们做到。
[1] 参见这三篇文章:《温柔地杀害他们——令撒但欢喜的同情心》,《同理心的诱人之过:撒但如何用同情毁坏我们》,以及《危险的怜悯心——如何使爱心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
[2] 苏珊·兰佐尼 (Susan Lanzoni),《同理心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mpathy"),大西洋网站,2015年10月15日。
[3] 朱迪思· A. 霍尔(Judith A. Hall)和瑞秋·施瓦茨(Rachel Schwartz),《同理心的现在和未来》("Empathy Present and Future"),《社会心理学期刊》159, no. 3: 225–43。
[4] 布琳·布朗(Brené Brown),《软弱的力量》("The Power of Vulnerability"),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 2013年7月4日视频。
[5] 词典将宽容定义为“容忍某事的能力或意愿,尤其是容忍自己不一定同意的观念或行为的存在。”现在思考一下在现代世界中打着宽容旗号的态度和行为。实际上,鲜有事物比“宽容”的现代概念更为“不宽容”。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魔鬼家书》中,位高的“私酷鬼”副部长描述了打着宽容旗号却隐藏着极权主义本相的恶魔策略。同样,如果有人对 “宽容之罪”提出警告,许多现代基督徒读者会直观地理解他的意思。
[6] 这也是我在最初写这个问题时使用《魔鬼家书》体裁的一个主要原因。《魔鬼家书》使用了恶魔的夸大言辞来揭示罪的微妙隐晦。同样,在《梦幻巴士》(我的另一篇文章有参考此书)中,路易斯将灰色小镇上被咒诅的灵魂描绘为真实人类的夸张版本。本质上他们是滑稽角色,但却凸显了真实人物的特征。在这些案例中,鬼魂和恶魔代表了我们自己在世上的罪的最终结果;他们显明了完全败坏时会发生的情况。
这样,通过夸张和讽刺的手法,我们仿佛在显微镜下更清楚地看见自己内心败坏的趋势和轨迹。路易斯向我们揭示了夸张的败坏的果实,我们便可以理解现今败坏的种子。换句话说,《魔鬼家书》体裁适用于揭露我们原本无异议的术语下的实际动态。鲜有基督徒会站出来说:“我在通过我的表现寻求上帝的接纳。”相反,我们谈论圣洁的重要性。圣经的话语成为了我们自义的面具。
这类通过《魔鬼家书》体裁揭下恶魔面具的一个典型例证是,路易斯对“无私”一词的观察。《魔鬼家书》提到了恶魔的语言学部队的成功,他们把基督教的“仁爱”美德替换为“无私 ”。 “无私”作为负面术语,强调我们缺乏什么。“仁爱”作为积极术语,强调了我们为他人益处所做的事。这种替换的价值在于,恶魔可以“教导一个人弃自己的利益不顾,不是因为别人得到这些利益后会感到幸福,而是因为舍弃这些利益会让他显得很无私”。
他继续提到无私在自义面具下的多种复杂的表现形式。一位家人提议说他们想出去吃饭。另一位家人(在无私的精神下)说:“我更喜欢在家吃,但我愿意出去吃”。第一个人,同样在无私的精神下,撤回了自己最初的提议,不想其他人给他小恩小惠,因此他改口说:“我愿意按照大家的想法来。”即刻,在无私的控制下,整个家庭都坚持表示愿意按照其他人的想法来。他们希望自己比别人表现得更加无私,结果“情绪被撩动起来……随后带来一场真正的争吵,双方都在苦毒怨恨中”(144页)。
此刻,有人也许会反驳:“但是路易斯,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无私的,反而正是自私的。他们的行为是极度地自私和自义。其他人不会用你的这种方式去定义无私。”毫无疑问,路易斯会回答:“确实如此。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宣扬他们的罪。嫉妒藏于公平和公义的面具下,贪婪被‘祝福和兴盛’的面具掩盖,懒惰则躲在尊重他人空间的愿望下,忙碌藏于爱邻舍和为他人牺牲的呼召下,骄傲和优越感藏在感恩里面 (‘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人……’)。魔鬼喜爱在无辜的词语中,尤其是美德的词汇内,隐藏真实的罪。魔鬼家书帮助我们看清俗语里的恶魔陷阱。”
[7] C. S. 路易斯,《荣耀之重:暨其他演讲》,英文版25页。
[8] 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写对同理心的批判之前,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个危险。(参见《温柔地杀害他们——令撒但欢喜的同情心》 )。有趣的是,尽管在那封信中,我让私酷鬼鼓励他的门生采用“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作为魔鬼策略的一部分来败坏同情心(挥舞着罗马书8:28作为武器对付受伤者),但是没有人反对我让魔鬼说出这句经文。 我怀疑这是因为我们都认识到,罗马书8:28中的荣耀可以被扭曲,并用没有爱的方式使用。我最近的几篇文章中也指出,同理心也会被类似地扭曲。
[9] 阿拉斯泰尔·罗伯茨,《勇气和同情心的伦理观》,Alastair's Adversaria 博客,2013年5月27日。
[10] 布琳·布朗(Brené Brown),《敢于领导》(Dare to Lead,纽约:兰登书屋,2018),英文版142页。
[11] 埃德温·弗里德曼(Edwin Friedman),《神经的失败:快速修复时代的领导力》 (A Failure of Nerve: Leadership in the Age of the Quick Fix, 纽约:西巴利,2007年),英文版133页。
[12] 同上,英文版136页。
[13] 阿拉斯泰尔·罗伯茨(Alastair Roberts),《自我与领导力:对埃德温•弗里德曼<神经的失败>的总结和探讨 》(Self and Leadership: A Summary of and Engagement with Edwin Friedman’s Failure of Nerve,自行出版,2016)。
[14] C.S.路易斯,《梦幻巴士》 (The Great Divorce, 1946;重印版,纽约:哈珀,2015),英文版136页。
[15] 贾斯汀·泰勒,《陶恕的矛盾和他的敬虔进路》( "Tozer's Contradiction and His Approach to Piety"),“两界之间”博客,2008年6月9日。
[16] 《梦幻巴士》,英文版106页。
[17] 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摆脱共情:理性让你更强大》(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本书中文版参见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译本。
[18] 汉娜·罗辛(Hanna Rosin),《同理心的终结》("The End of Empathy"),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19年4月15日;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同理的关注实际上会加剧政治分化吗?》( "Can Empathetic Concern Actually Increase Political Polarization?"),科学美国人杂志,2019年11月6日;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同理心正在分裂我们》("Empathy Is Tearing Us Apart"),连线杂志,2019年11月9日。
[19] 亚比该·多兹(Abigail Dodds),“从同理心到混乱:后现代时期教会的考虑”("From Empathy to Chaos: Considerations for the Church in a Postmodern Age"),“希望与停留”博客(Hope and Stay),2019年6月18日。同时也参见多兹,《同理心的美好与滥用:美德如何变成了暴君》("The Beauty and Abuse of Empathy: How Virtue Becomes a Tyrant"), 渴慕神网站,2020年4月14日。
译:穆汐姊妹团;校:JFX。原文刊载于“渴慕神”英文网站:Do you feel my pain? Empathy, Sympathy and Dangerous Virt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