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议的那样,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读者“让这几个世纪以来干净的海风吹过我们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译注)。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接下来要审视一些可能被遗忘、但是依然和现今的教会相关,并且能帮助今日基督徒的经典著作。本文是邸立基所著《神学第一步》(A Little Exercise for Young Theologians)的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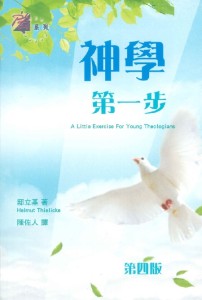 试着把这本小书想像为一张贺卡,它的首要作用是给到那些刚踏上攻读神学第一学期的人,祝贺他们一路顺风(bon voyage)。同样地,这本书亦可作为祝贺“周年快乐”之用,对那些诚实的牧者,愿意谦卑地回顾反省自己是否达到最初的目标。另外,此书又可用作祝那些骄傲自大神学家“痊愈”的贺卡,或极端点说,这可作为一张慰问卡,安慰那些已经忘记整个神学任务所应有的兴奋与应许的人。
试着把这本小书想像为一张贺卡,它的首要作用是给到那些刚踏上攻读神学第一学期的人,祝贺他们一路顺风(bon voyage)。同样地,这本书亦可作为祝贺“周年快乐”之用,对那些诚实的牧者,愿意谦卑地回顾反省自己是否达到最初的目标。另外,此书又可用作祝那些骄傲自大神学家“痊愈”的贺卡,或极端点说,这可作为一张慰问卡,安慰那些已经忘记整个神学任务所应有的兴奋与应许的人。
在刚才那段文字里,“神学”一词曾出现三种不同的版本(神学、神学家、神学任务——译注),故此便细致地反映了本书的宗旨:作者以清晰有力的语言,来表述深奥的神学语言。如果本书只用以欢迎年轻的神学家,那它就不会长久被当做纪念品来收藏。我们必须经常重读此书,才能穷尽它的意义。作者期望那些初出道的神学家能从中获得有用的规劝。
任何人在接受劝告之前,很自然地会审查辅导者的资格。看看他凭什么这样说,究竟他会向我说教?抑或将他的意见渐渐渗透进我的意识?他会否装腔作势?还是假作慈悲?在这情况下,他是否就知道神学与青年神学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在基督教的圈子中,鲜有人会像邸立基(Helmut Thielicke)般令我们给予毫不犹豫的信任。他身穿数个职事的礼袍,而且全部都称身如意。譬如最近他出任德国汉堡大学的校长,需要负责一般行政职务,正如他在书中述及,另外他亦要穿上具有历史性的学术袍子。作为实用神学家,他要穿上教授的袍子,以便从事基督教伦理的讲授工作。大部分读者最喜爱的是他穿上讲道袍的样子,有些人则将他列为世界上最伟大讲道家之一,众所周知,每星期两次在世俗化汉堡城的偌大教堂,都因他讲道的吸引而挤满了人,德国的教章与杂志都可为此作证。他的讲章现已有许多印刊成书,是许多传道人拿来充实自己的少数书籍之一。最后,我们可以想象邸立基穿上灯芯绒的运动外套,作为旅行家与说故事者,但不论是什么角色,他都是挥洒自如,而这些都成为他在这里说话的合格地位。
作为学术、认真与关怀的人,邸立基赢得他读者的信任。他在本书中向青年神学生所说的话,鲜有人可以带有这样厉害的话,而仍然是充满恩惠与医治。无疑在欧陆神学日新月异的领域中,鲜有比他更为敏锐的神学家,在美国务实教会生活的广阔道路上,可能有较他更为能干的行政人员,但鲜有人可以像他一样将严谨综合的学术研究结合于教会事工。这种综合在今天的欧洲是特别需要,而我相信从另一角度来看,在西半球的一方亦是照样受欢迎的。
邸立基教授生于一九〇八年,接受了传统博大高深的德国神学教育。他于一九三〇年代经历了一次个人危机,当时正值他的事业如日方中,但却面临着“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即纳粹)的威吓。他对纳粹主义(Nazism)的反抗使他赢得了新的发言权,自从二次大战以来,邸立基日益受人重视。毫无疑问,阅读过本书而经验丰富的神学家与教牧人员的书架上,一定会收藏了他的其他多本著述,反映了邸立基本人的广泛兴趣:《上帝与撒但之间》(Between God and Satan),《上帝的沉静》(The Silence of God),《我们在天上的父》(Our Heavenly Father),《等待的慈父》(The Waiting Father),《世界如何开始》(How the World Began),《基督与生命的意义》(Christ and the Meaning of Life),《论虚无主义》(Nihilism),还有他对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德国新约神学家)的深邃回应。神学的初来者会很快地拥有与阅读这些著述,并努力耕耘于他的庞大德文钜著《伦理学》,或者是耐心地等待此书的英文翻译(编者按:此书已译成英文:Theological Ethics, 3 vol. set 1996, Fortress Press)。邸立基的写作速度可以说是不下于我们的阅读速度。
以上的生平概略并不是想藉此使读者感到尴尬,而是想指出邸立基所具备的多种独特优点是罕见的,并且是他所从事的,向人作出忠告的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神学对他来说是具备理论与道德的责任,你会看到他一方面定义神学为“反省”(reflection),另一方面又形容它为“意识”(conscience)。他的作品反映了内部的一致性,显明邸立基的各种表述意义都是源自同一放射中心——就是反省与意识。
当然,作者的条件亦为他的立论带来不利的影响,他那过分强硬的作风有时盖过了其他观点的可能性。例如,他的基督徒意识过早压倒了他在《论虚无主义》中所了解的虚无主义者。另外,他对比喻的解释亦是教人感到诧异,然后当读者参阅了经文及其他各种仔细对意义的探讨后,例如耶尼米亚(Joachim Jeremias)与陶德(C. H. Dodd)等的著述,便可发现这些解释可能较其忠于比喻的原意,邸立基的直观与直觉是如此多姿多彩,以致一些意义与准确层面可能因此受损。
邸立基博士形容这书为“神学小习作”(A Little Exercise for Theologians);其中是他在职责上为自己学科开设的研讨课。我认为出版商有智慧地保留了本书的亲切风格,他们保留了许多只是对原来听众,而不是美国的受众有意义的地方,但因此我们却好像亲身聆听了我们极希望亲自出席的授课,这便使我们不会觉得是在接受一些无缘无故的忠告。邸立基称这为“习作”,在其心里想着的是依格那修(Ignatius Loyola)的“属灵操练”(Spiritual Exercise)及其他基督教自我修练的习作。我对此书有如下描述:这是一本有关神学上自我操练的课本,这可能只算是这博大领域的“小习作”;或可视为一出《小夜曲》,或在壁画底下留下的一些笔触,但这却在最微小的形式上可以显明整体。在舞台剧中微音发出的提示可以间接显明其他直接的台词,这里就是邸立基对神学听众的提示。
介绍书籍的人常常面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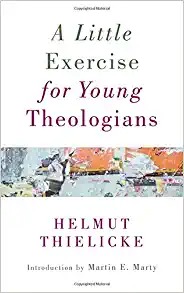 的诱惑,就是尝试预测或重复书中内容,但我却宁愿与其论证对话。对于那些自觉正在或已经成为神学家的美国基督徒来说,他们是否会同样碰见本书所述及的问题?如其所述,欧陆的神学家,相对于其美国的伙伴来说,泰半活在象牙塔内;该处的活跃份子的积极性较低,那里的神学不太关切教会的生活,只是关切严谨、科学与卓越的学术。在布道、教会治理、牧养关怀、行政等方面,美国的教会都是遥遥领先的。
的诱惑,就是尝试预测或重复书中内容,但我却宁愿与其论证对话。对于那些自觉正在或已经成为神学家的美国基督徒来说,他们是否会同样碰见本书所述及的问题?如其所述,欧陆的神学家,相对于其美国的伙伴来说,泰半活在象牙塔内;该处的活跃份子的积极性较低,那里的神学不太关切教会的生活,只是关切严谨、科学与卓越的学术。在布道、教会治理、牧养关怀、行政等方面,美国的教会都是遥遥领先的。
但传统的图画正在不断改变。德国神学家因着希特勒时代的冲击,唤起了无比的勇气,冲出他们的象牙塔,而他们亦不能再走回头路,因为在战后宗教信仰如何适切世俗化世界的挑战日益紧迫,与此同时,欧洲的教牧需要更努力的工作,才能获得别人的重视,维系与牧养他的羊群。
在美国,神学家在战后亦有相同的任务,他是向“外人”,不单是向神学家说话。务实的教会工作者可能较其没有经历战后宗教复兴的欧洲同僚更为驾轻就熟,这至少是从表面上来看。不过,在大西洋两岸的神学家与教牧人员使命的差异,已经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程度上而已,这样的日子指日可待。
尽管上述的张力日渐松弛,神学的探索与行动的分享,与及支持它们的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可悲鸿沟仍然存在。信徒会众甚少承认或信任神学学问的价值,而神学学者亦甚少同情日日辛劳的牧者。基督教容许不同的恩赐,只是有同一圣灵,在同一群人中,我们会允许与鼓励某些恩赐与才干。邸立基便是在此论证每位耶稣基督的仆人都需要是自我操练的神学家与身体力行的教会工人。这是他的小习作的另一关怀。
除却邸立基的大纲,我尝试构想谁是神学在美国的敌人。首先是潜进教会圈子的普遍不信任气氛,它规劝人回避神学,其忠告是:基督教的信仰经不起智性的考验,故此尽管忙碌吧,但不要分析与细察基督教的立场,这样就可以生存下去。其次,一股冷漠感或短视正伸进教会的许多关键性的行动。只要不是马上影响我教区范围中教会四堵墙内的生活,我便不加理会。另外一个敌人就是将“行动家”(doer)加以偶像化,以之与“思想家”(thinker)相对立。那些能言善辩、长袖善舞的人总是较那些只会钻研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技工,能建起更多的房子,筹募更多的经费及宣讲更响亮的讲章。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毫不介怀其所做的会导致基督与生活意义、信仰与其他事物之间更大的割离,只要他的宣传机器不停喷烟,他的布道车轮运转不停便心满意足了。最后,我避免对此点言过其实,就是在美国宗教中存在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流传于十九世纪对上帝敬虔与热心的追寻,或是二十世纪因着相对主义冲击下而产生的宗教副产品。
任何人若想在美国从事神学,按着邸立基的指引,他必须同情这些神学的敌人。上文所说互不信任的关系是大有道理的,首先是因着神学本身的限制而引起的不安,神学并不能时常解答一切问题,它不能解释启示没有说明的事情,像“什么是恶的本体来源?”等问题。另一些时候,理智所倾向的虚假答案亦常常叫人不能自己,自高自大。公元四世纪西西古斯(Cyzicus)主教优诺姆斯(Eunomius)曾言:“我认识上帝甚如上帝认识自己”,他许多时候似乎成了神学家的护守圣者。对普通基督徒与忙的不知其所以的教牧人员来说,将自己从教会生活与具体实况中抽离的倾向,可说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可悲误解。事实上神学家知道更多与经验更多时,便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这也会有时造成互不信任的情况,虽然事情不该如此,但我们不要忘记只有上帝才拥有完全的真理。毫无疑问,最常招惹批评的自然是神学家所特有的专业术语、暗语与隐语。我们欣然接受医学上的专业术语(有谁喜欢被笼统的断症为“胃痛“?),或科学的专业名词(连小孩子也能说出”洲际弹道飞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s missile”),但一旦关乎纯净福音时,我们却对此绝不信任。邸立基在此点的忠告深具智慧。
不论神学的敌人是谁,或有任何导致彼此不信任的理由,教会却应负起神学的必然任务,这便是我们的使命:尽“意”(或“心思”,mind)爱主你的上帝。世界正不断转变,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语言与意义上的基本探索层出不穷,难道我们要为信仰建起细小的栅栏,或是高高的墙垣?还是信仰应面对广大而繁复的世界?神学的任务具有内在的意涵:深入而浅出、承担与见证。神学是无可避免的,问题它该是好抑是坏?有意识的抑是无意识的?自律的抑是松散的?
在美国处境中关心上述问题的,必会乐于看见邸立基教授这本忠告的英文翻译。我们现在正面临危机,就是信封大于贺卡,闹哄哄的支撑着应该进行操练的场所。如何克服写作过长引言的试探实在不易。属灵操练需要人的回应、争论与委身,若果它能在某些读者的心灵中,不管他们是否神学家,或是否青年人,只要能唤起相同的诱惑,本书便可说是达到了其应有的目标。
本文系《神学第一步》(陈佐人译,香港卓越书楼,1991)引言,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German Antidote Against America's Theological Ene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