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试通过本文探讨一个略微复杂、且可能颇有争议的问题。我不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信仰与政治的关系”或“政教关系”。因为,当我如此陈述时,已然隐藏了某种“二元论”的前提,暗示“信仰”与“政治”或“教会”与“政府”首先是区隔、对立的两个领域。
我把这个问题表述为“福音的政治维度”。我希望表达的是:在福音的涵义中,原本就包含了政治的维度,并且能够形成切实的实践,而无须(无论有意无意)借助现代世界的政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构成与之“对抗”)。这个命题当然需要非常小心地解释,因为它可能引起许多误解。
我需要先提出本文的首要意图,是希望基于圣经、从一个可能被忽视的角度出发,对福音信息作一探讨。并且我相信,这个探讨对于基督徒在现代世界的信仰实践是有意义的。
首先,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新约中,耶稣和使徒们都对福音作了异常丰富的表达,从形式到内容(当然,福音的核心坚固不变)。那些福音表达有别于现代基督徒常常被教授或灌输的“单张式信仰陈述”。在新约的福音表达中,我们能够相当容易地辨识出许多主题和意象,不同的主题和意象从不同的角度向圣经的读者展现福音,比如:“神拯救、赎回祂的子民”、“约的实现”、“献祭的完成”、“神国度的降临”、“回归到神的园子”、“进入神的筵席”、“神栽种和收割庄稼”、“神带领、牧养、寻回羊群”,等等。可是,我们比较少地明确指出,这作为福音呈现的种种图景,其中包含了清晰的政治因素。很多时候,即便当我们提及明显的政治性词汇(比方“神的国”)时,也会倾向于对其作一种“非政治”的解释。
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理解和“再呈现”,是否已经足够努力地反映了圣经本身的表达?毕竟,在耶稣和使徒们的福音呈现中,充满了“国”、“军队”、“王”、“审判”、“正义”这类元素。这些元素,难道首先不是政治性的吗?甚至,“教会”这个词,当它表示“人群的聚集”时,本来首先就是指政治性的集会,而非出于民族、经济、教育这类原因形成的聚集。同样,保罗也花费了许多笔墨,谈论教会的治理。诚然,耶稣和使徒们也都强调了某种对“政治性理解”的矫正,比方“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但即使在这个表述中,仍然是以肯定的方式使用“国度”这样的词,只是指出它“不属这世界”。
所以,我们是否错过了一些什么?保罗这样说(以弗所书2:11-19):
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保罗在这里自然是作了一个精彩且清楚明白的福音表达:基督的福音使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群体,外邦人与犹太人,合一了。在这个福音表达中,有若干重要的主题,比如诸约、献祭、律法、和平。可是,还有一个主题也同样很明显,就是“国”。12节,保罗说外邦人原本的生存状态,与神隔绝、没有关系,“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此处他的用词是"πολιτεία"。这个词在古代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指城邦政制、公民身份,也可用于指称更广泛意义上的秩序。19节,保罗先是提到,因着福音,外邦人就不再是“外人”(ξένος)和“客旅”(πάροικος)。在古代语境中,这两个词,前者是指(有可能根据条约,或是传统的待客习俗)长期居住在城邦中、享有很多福利但不具有公民权的外来者,后者则指完全的外来者、陌生人,两者与国民在政治地位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差异。保罗继续说,现在他们成了“同国里的人”(συμπολίτης)。这个词的意思是“公民同胞”,即同一城邦的公民。
所以,保罗在这个段落中,接连运用了几个字词,都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涵义。借助这些词汇,保罗描绘的图景是:在某种意义上,福音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适合使用政治词汇来描述的关系和结构。现代读者可能有一种直觉,把这里的表达认作“比喻”。但是,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是:保罗这样说的时候,教会还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现象,或者说,当时的读者并不像现代读者那样有一个清晰的意识,认为“教会”是与政治团体截然不同的机构/组织。所以,大约现代人更能接受这是一个“比喻”,而对当时的读者而言,这里几乎找不到“喻体”。古代的读者(尤其是希腊人,而保罗这番话又正是在对希腊人讲的)不太可能错过这个福音表达中明显的政治意味。
另一个至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约中“教会”(ἐκκλησία)一词的运用。这个词本身就是指城邦的公民大会,一个享有最高权力的政治集会。对当时的希腊人而言,这个词的政治意味非常强,而新约恰恰用这个词来指称教会。
福音书中,只有马太福音16章和18章,耶稣两次提到“教会”,两次都谈论教会的权柄,后一次甚至是很具体的惩戒程序。使徒行传第一次提到“教会”,则是在第五章,刚刚发生亚拿尼亚夫妇不服从使徒、遭罚而死,“全教会都惧怕”。
因此,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思考:如果新约希望对福音作一种“与政治无关”的表达,为何如此直接而不加解释地运用政治词汇?至少,我们有理由说,政治图景是新约用来描绘、呈现福音的众多图景中的一幅,而且,看起来它绝非比较不重要的那一个。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考察圣经,并对自己惯常的预设加以反思。自文艺复兴以降,一个显著的过程是所谓“政治”的领域逐渐独立,形成了一套自主的规则、话语、价值、论证。这正是需要反思的:圣经如何界定政治?
马太福音12:22-32: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哑又瞎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但赶逐撒但,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 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这是特别有趣的一个段落。通常,基督徒们的注意力都被难解的“亵渎圣灵”问题抓住,进而注意整段谈到“赶鬼”这类属灵的事件,反而错过了耶稣在这个段落中表达的强烈的政治涵义。
这个段落始于耶稣的一次赶鬼行动,众人并不很有意识地宣布祂是“大卫的子孙”,以色列王权的拥有者。作为敌对方出现的法利赛人表示,耶稣的权力来自于“鬼王”(ἄρχοντι τῶν δαιμονίων)。耶稣对此的回应,谈到“国”(βασιλεία,王国)、“城”(πόλις,城邦)和“家”(οἰκία,家庭),这三个词也就是古代人对政治秩序发生路径的认识,从家到城邦,再到城邦联盟或王国。耶稣指出在这三类政治体中,有一种情况将完全地破坏秩序,就是“自相纷争”,分裂,亦即内乱。这一点同样是古代人的政治共识。28节,耶稣说,如今在各位眼前发生的,是一种秩序的根本性转变,神国(βασιλεία τοῦ θεοῦ)的秩序当然不可能有内乱,因为带来新秩序的圣灵不可能与神不合,也就取消了内乱的根源。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31节耶稣说“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恐怕也有一层含义是,对带来合一的圣灵的攻击就等于否定或矮化神国的总体秩序,不承认神国、神的统治,不接受人进入神国的方式由神规定,自然是“不能得救”的大罪。
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常被忽视的30节。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这句话紧邻着“亵渎圣灵”,或许也是被忽视的原因之一。然而,这句话正说明了神国秩序(政治)的原则。当神国来到的时候,将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收聚”(συνάγω)与“分散”(σκορπίζω)。一个人群将被聚集起来,在此之外的,就都分散。而决定或带来这一聚集的,也决定了这两种状态区分的,是耶稣自己。凡是与耶稣相合,就聚集起来,并且参与他的收聚行动;凡是不与耶稣相合的,就分散。耶稣使用了许多明显的政治词汇,来描述和呈现神国秩序的建立,也就是一种因他而有的、人群的“聚集”和“分散”状态。福音在此世的效果,也就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福音的政治表达,也就是因基督而有的人群聚集与区隔。
进一步,基督如何实现他对人群的“聚集”和“分散”呢?在这个段落的上文,给了答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马太福音12:17-21说道:
“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不争竞,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耶稣建立神国秩序的方式,是祂的降卑、怜悯和公义。圣子进入世界,成为人的样式,存心谦卑,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代赎完全,第三日复活,叫那些不靠行为、只靠信心的人,得以领受祂白白的恩典。于是,人群分开,教会建立,神国在这世上被人看见,显出神的荣耀来。将来基督还要来施行审判,将神国完全显现出来。
圣经确实向我们描绘了一种政治图景,但它对神国秩序的定义,乃是以道成肉身、为人牺牲的圣子耶稣为中心。神国政治图景的展开(人群的聚集与分散),同样是以降卑受苦的基督为中心,进入神国的人,也将效法耶稣受苦的样式。在这一点上,神国的政治就与这世界的政治截然不同。
不过,若我们观察今日的世界,却又会发现存在一种极大的艰难。
如前所述,圣经使我们看见,对于福音,能够作一种带有强烈政治意涵的表述和呈现,即神国秩序因基督来到、圣灵的工作而牢固地建立起来,人群被分开。这就是政治。可是,我们需要思考,为何今日我们谈论福音/信仰/教会与“政治”的联系会产生相当的顾虑?既然圣经向我们呈现了一幅政治图景,那么,它在此世的生活中为何模糊不清?
事实上,圣经亦向我们指明了福音政治图景遭遇的危险。启示录13章描绘了魔鬼在世间的行动:大红龙站在海边,从海中上来一个兽;兽有七头,其中一个头“似乎受了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跟从兽,又敬拜龙与兽;又有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能够行前一个兽的权柄,它给人受了一个“印记”。
尽管这个段落充满了奇异的图像和符号,但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值得注意,就是魔鬼不断地模仿、装扮三一神的存有和行动。龙扮作圣父,第一个兽扮作圣子基督,第二个兽扮作圣灵。它们模仿了基督的死和复活,模仿了圣灵降下与改变人心,模仿了招聚人来敬拜。有许多人会被迷惑,去崇拜魔鬼。他们之所以被迷惑,是因为魔鬼相当成功地伪装成了三一神。
这样,我们可以略微反思,为何圣经呈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国政治秩序”,今日很少有人谈论。一个相对简单的回答就是:魔鬼在此世的活动模仿了神国的政治秩序,令人对此产生了很大的迷惑。
按照极简的历史叙述,教会建立之初,事实上就表现为一个具有清晰外部边界和内部治理结构、形成特定秩序的共同体。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马这个已经很成熟的此世政治体遭遇了一个带来强烈陌生感的群体,罗马人意识到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迄今为止能够包容(或压制)一切民族、风俗、宗教的帝国无法包容它。于是,就必须消灭它。
而当君士坦丁声称归主,就启动了一个新的进程,一方面看来似乎帝国比原先的立场大大后退,不再逼迫教会,甚至使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另一方面则开始了两种秩序的沟通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帝国通过模仿教会而消除了起初遭遇的那种不可磨灭、无法回避的陌生感。二者之间的这种沟通到中世纪逐渐进展为国家-教会的二元结构,进一步又在双方之间造成了许多观念的融合、借鉴、交换、平移。到中世纪晚期,我们可以看见,与教会世俗化进程同步发生的,恰恰也就是国家的神圣化。由此,更进一步,在一种与教会和神学有着深刻纠缠的国家形态之基础上,现代世界逐渐成型。
现代国家形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体,事实上,它在许多方面、在相当的深度上“模仿”了基督教会,比如:某种“建国神话”(尤其以“出埃及”式的解放叙事为代表),被奉为神圣的经典文本(可能是革命宣言或一部宪法),先知/君王式的开国元勋(呈现为纪念碑、石像甚或“不朽”的肉身),不断“生产真理”的机制(学者扮演祭司的角色),要求成员效忠(宣誓),对“敌人”的识别与严厉斗争,大众参与的特别节日和仪式,等等。
如果我们同意前面所述,福音的政治性体现于一种以基督为中心(标准和动力)的人群“聚集”和“分散”,具体形式就是教会。那么,现代国家则是以另一些东西为中心(很不同的标准和动力),构成人群的“聚集”和“分散”,具体形式就是民族国家。在现代国家中,可能首先以民族认同或者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共同体,而其背后隐藏的那些不同的动力,正好反过来定义了现代的“政治”,也由此确立了政治与信仰领域的区隔。这类动力,可能被解释为人对利益或荣耀的追逐,可能是恐惧的激情,可能是经济的需要,可能是群居的本能,等等。对于这类因素的探讨,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知识和文献,就划定了一个与宗教无关的政治领域。
如果我们同意,圣经提示了魔鬼善于模仿神,那么,就有必要反思基督的教会在现代世界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教会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现代国家对政治的种种定义和操作,由于这类定义和操作表面上与基督教信仰颇有相似之处,若教会欣然接受之,就可能引起更多的问题。比方,现代国家建立在识别绝对敌人的基础上,识别的标准一定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教会遭遇这类观念时,由于“与敌人争战”、“人群要分开”的心态乍看起来与圣经教导有相似相通之处,就有可能接受,却对背后的标准和动力反思不足。
最大的危险在于:教会可能偏离基督的福音,把另一些东西(甚至可能是“福音的果子”)当作人群“聚集”和“分散”的标准及动力,“爱的感觉”、社会公平、某个政党的政治纲领、物质的繁荣、恰当的教育,都可能进入这个清单。与之相对应,教会在现代世界却日益失去了以明白无疑和正式的方式确定、处理真正异端的能力。因此,情况可能变成:一方面,异端层出不穷、得不到有效处置,另一方面,持有正统信仰的基督徒之间,却常以对待异端的方式彼此为敌。教会在现代世界无力展现出起初那种令世人感到陌生的、福音的政治维度;教会至多只是踏进世界的政治领域、以世界熟悉的政治和文化定义开展某些行动(哪怕行动本身表现得很“激烈”,或者“很有成果”)。
如果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应付”这世界的政治形势,那么,就有必要再次回想宗教改革。因为,真正令宗教改革形成不可阻挡之势的,并非对罗马教会腐败及教会介入世俗政治的批评,而是关于重要神学议题的思索、分辨与论证。
改教家们最为关心,甚至不惜闹到彼此分开的议题,第一,世人究竟如何得救,如何判断是否得救;第二,是圣礼究竟有几个,具体要怎样施行。如果从“福音的政治维度”出发观察改教家们的关注点,不难看到,这两方面的神学议题,在实践中一定会很快指向对教会共同体的辨识与规管——人群因何聚集、如何聚集、又如何分开。换句话说,宗教改革宣称乃是恢复真正的基督教、回到本源,从这个角度观察,也就是恢复了圣经所讲论、规定的“聚集”与“分散”,亦即恢复了福音正确的政治维度。相较之下,当时罗马教会的错误,虽然表现在贩卖赎罪券、教廷专权、教士腐败之类的现象,但更深的错误,一定在于对福音的认识和表达。在这一点上,当罗马教会日益追逐此世的权力和荣耀,也就离降卑牺牲的耶稣基督日益遥远,离基督这个福音政治维度的内在根基日益遥远。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展开,对救恩论与圣礼的关心,进一步体现于圣经论。因着追求更清晰、更符合神命令的救恩论与圣礼,必然不断推动对圣经作为权威的敬虔心态,与研究、翻译、教导圣经的热情。而圣经的翻译和研究则继续反过来推动教会的改革。
不过,罪人总是容易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基督徒们的注意力似乎越来越从改教家们起初关心的救恩、圣礼、教会和圣经的限定,转向这世界发生的事。这或许是现时代基督徒们面临的更大问题。如果“如何进入世界”成为常常要考虑的事,那么,大有可能,基督徒们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世界的现象、潮流、“风”本就是变动不居的。基督徒们虽然绞尽脑汁、终日辛劳,最大的感受却可能是常常询问:“又有新变化了,我们要怎样调整呢?”、“牧师你懂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吗?”这世界的政治形势、政治“信条”、政治文化在不断改变,基督徒们能够做什么呢?抓到了某个现象,或借鉴、或反对,然后又会有新的现象出现,期待着另一种不同的反应。教会以如此方式日益进入世界,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坚定根基,因为这样的进入方式本身就意味着随着现象不断改变。这恰恰不是宗教改革对“改革”的定义。
当然,时代在变化,环境不同了。可是,我们仍然应当像当年的改教家那样,渴慕并竭尽全力“回到”圣经的本源。若论到政治,今日我们仍然应当竭尽全力恢复圣经所展现的福音的政治之维。今日,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聚集与分开?能够对这个世界纷繁复杂、快速变动的(政治)现象作出回应的,依旧是古旧的福音。改教家极度重视的圣经与圣礼,仍然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今日,高举圣经,意味着释经讲道;严肃对待圣礼,意味着教会建制。圣经和圣礼是基本的信条;释经讲道和教会建制是在处境中谨慎的应用。
讲道者应当怀着圣经所说的忌邪之心,万分严谨地对待经文,运用适当的方法将文本解开,并接受由此而来的教导。讲道者严谨地释经,同时又是在建造教会,以圣言招聚神的子民——“聚集”起来,听神的话,且要顺服,然后,“天天彼此相劝”。一个以圣道为中心的基督徒群体,必然接受由神的话管理自己,而非操纵神的话以实现其目的。
至于圣礼,洗礼有一重要涵义,即确认并宣告一个人为基督的门徒,接纳他加入基督的身体。而圣餐,则有一方面的含义,就是确认这个人与基督联合,继续地保持在基督的身体中。从这些意义观察,圣礼事实上构成并维护了神子民群体的边界。一间以敬畏之心施行圣礼的教会,必然询问“圣礼的意义为何”、“谁能施行圣礼”、“谁能领受圣礼”这些问题。教会的建制并非出于管理的方便,而是福音政治维度的必然结果。
圣道与圣礼的正确施行,又与圣灵的工作不能分开。真信徒必然有圣灵内住;没有真信心的人,必然没有圣灵。有圣灵内住者,必然听见了神的道就顺服,也必然领受圣礼的诸般好处;反之,则必然表现出对圣道的敌视,也必须被排除在圣礼之外。圣灵的工作绝不与圣道和圣礼相悖,并由此区分神的子民群体;圣灵的工作则显明和招聚以及驱除那些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所有这些综合起来,仍然回到福音的政治维度,回到福音使人群发生的聚集与分开。
最后,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正确地施行圣道与圣礼,也就是不断传讲和见证那位降卑、受苦和牺牲的基督。正是基督自己,使得人群所发生的如此聚集与分开,与世界中发生的聚集与分开完全不同。
教会不需要因为自己在这世界的政治活动中显得格格不入而感到抱歉。严格说来,教会不需要做些什么,向世人证明福音除了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还要加上任何东西、任何行为或信念。教会不需要被人的设想、愿望和情感牵引着进入世界、改变这世界的政治,教会只是单纯地以其存在本身,迫使世人观看、遭遇一种陌生、却是纯良与美好的秩序,迫使世人观看圣经所说的罪如何得到处理,迫使世人观看永生神的荣耀如何在一群罪人身上显露出来。也唯有如此,教会才能有意识地分辨和击败撒但对神和神国秩序的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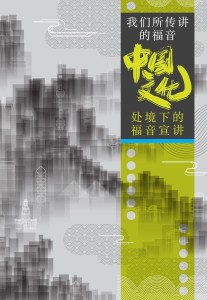 今日世界的政治,变化极快且多端。人群分分合合,人们找到敌人并与之战斗,然后发现如此敌对的背后,竟隐藏着深深的虚无,进而不得不以持续不断地敌我区分来掩盖这虚无,似乎如此还能赋予自己一点生气。人必须用敌人来作自我定义,因为自己的脚下没有根基可以依靠。
今日世界的政治,变化极快且多端。人群分分合合,人们找到敌人并与之战斗,然后发现如此敌对的背后,竟隐藏着深深的虚无,进而不得不以持续不断地敌我区分来掩盖这虚无,似乎如此还能赋予自己一点生气。人必须用敌人来作自我定义,因为自己的脚下没有根基可以依靠。
一方面,教会不能脱离这世界,不能拒绝谈论政治;另一方面,教会亦不能将自身的任务辨识为简单地进入世界、赞同或反对某种政治。教会好像一个天国的空间,在这世界打开,它在这世界,又不属于这世界。在这里,人群以世人无法想象、不能理解的方式聚集和分开,其目的都是为了传扬和敬拜那位降卑受苦、死于十架的基督。
撒但或许可以模仿基督的死与复活,却绝不能模仿十字架,因为撒但至终乃是意图窃取神的荣耀,他不能理解圣子放弃荣耀、为罪人走上十字架的恩典。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复杂、令人沮丧的环境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单单需要基督的福音。基督呼召一个人,乃是呼召他来效法自己,呼召他背起十字架,呼召他来受死。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并非只是“不从国教”,在其深处的,乃是自愿受苦、甘心背十字架的心志。在我们之前的许多圣徒,或许没有很好的神学,但他们出色地向世人表达了福音的陌生感。今日,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或许特别需要考虑在有清晰神学的基础上作出同样的表达。
编注:本文摘自《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中国文化处境下的福音宣讲》,该书由吉隆坡归正福音资源中心于2020年出版,您可以在这里下载本文的中文 | 英文PD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