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负面词汇。今天,复兴与(半)伯拉纠主义、美国个人主义和电视布道家联系在一起。许多人觉得这些联系令人感到不适——特别是那些深深认同改革宗神学的年轻归正者,他们对大复兴诉诸情感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因此,尽管许多人欣赏爱德华兹、怀特腓和第一次大觉醒,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后续发生在美国的复兴事件描述为人为的煽动、兴起异端、个人崇拜和情感放纵。他们认为,最好把所有这些玩意都丢到垃圾箱里,然后继续“照着圣经”延续传扬福音和建立教会的使命。我这样说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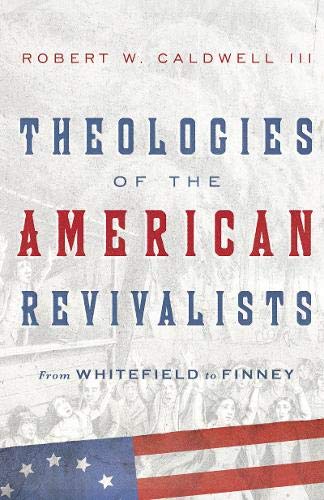 这种思潮的确有一些正确的神学洞见,但也有不少对历史的错误理解。首先,奋兴家并不都是不讲神学的实用主义者。从1740年到1840年,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们认真思考了复兴问题,包括归信如何发生、福音应该如何传讲,以及救恩论如何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我在最近出版的《美国奋兴家的神学:从怀特腓到芬尼》(Theologies of the American Revivalists: From Whitefield to Finney)一书中专门讲论了这一时期。
这种思潮的确有一些正确的神学洞见,但也有不少对历史的错误理解。首先,奋兴家并不都是不讲神学的实用主义者。从1740年到1840年,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们认真思考了复兴问题,包括归信如何发生、福音应该如何传讲,以及救恩论如何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我在最近出版的《美国奋兴家的神学:从怀特腓到芬尼》(Theologies of the American Revivalists: From Whitefield to Finney)一书中专门讲论了这一时期。
一些批评复兴的人认为,复兴运动与新教精神格格不入。新教基督徒在奋兴会上被启蒙运动、宗教狂热、现代主义、个人主义,或上述一些因素的混杂所迷惑。诚然,大觉醒——18和19世纪发生在美洲大陆的属灵复兴——帮助创造了被称为“福音派”这一强调归信的新教基督徒群体,它的边界和定义都是模糊的。但如果认为福音派以及催生它的复兴运动是一种对新教精神的扭曲,这是对历史的误解。
我提出的是相反的论点。复兴运动给新教带来了真正的兴盛,这正是因为复兴运动强化和扩展了新教的核心主题。当福音派通过大觉醒从其新教中脱颖而出时,它将新教所能提供给世界的一些最佳本质特征发扬光大。
改教时期的新教与复兴运动中的福音派之间有许多延续性,例如强调讲道、归信和宣教使命。复兴运动强化并扩大了这三个重点,创造了新的东西(福音派),同时又与宗教改革保持着深厚的联系。
宗教改革的新教基督徒和大觉醒运动中的福音派都强调了宣讲圣经的核心地位。苏黎世改革家茨温利开创了解经式讲道,因为他坚信上帝的话语需要完整地被传给上帝的子民。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教堂建筑把圣道放在首位:讲台的中心位置,因此注意力自然会被吸引到传道人身上。
美洲奋兴家对圣经也抱有同样态度。他们也宣扬同样的基本信息:不要相信自己的行为,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因此得救。简而言之,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和唯独信心(Sola fide)是宗教改革和复兴运动的基本标志。与此同时,复兴运动强化了讲道中的几个主题,产生了新的东西,主要有三:
第一,强烈的情感。
首先,虽然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都强调生动的讲道,但大觉醒运动中的布道家通常将福音信息的情感强度提高了几个档次,戏剧性地描绘了罪人的困境、神的愤怒和新生命的必要性。
这些讲道有一些已经成了传奇般的存在。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爱德华兹如何在讲道中提到蜘蛛:“神把你丢进地狱的深坑里,就像一个人把蜘蛛或一些讨厌的昆虫丢在火上一样。神恨恶你,被你的恶行激怒。”还有一些讲章没有进入福音派的历史记忆,但同样有力。以费城的“新学派”(New School,指赞成奋兴运动的长老会)长老会牧师阿尔伯特·巴恩斯(1798-1870)的讲道如何结束为例:
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知道你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结局。……如果你走向灭亡,我不得不坐下来哭泣,因为我看着你们正滑向死亡之湖。然而,我不能看着你跳下去,我不能看着你死——而且是永远地死——却不再次向你保证,福音是白白给你的。当你在那致命的边缘徘徊时,拒绝福音就是关闭生命、希望和幸福,我将再次大声宣告:看那!罪人们!看向一位慈爱的上帝。祂现在来到你身边。……为了祂,我要向你呼吁,我有一种深深的感觉:你在他的手中,你要被神的道约束、今天就悔改,要相信福音!如果你灭亡,这责任完全是你自己的!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奋兴家在大觉醒中培养的强大修辞技巧,这些技巧今天仍在美国的讲台上可以听到。
第二,讲道的主题。
第二,讲道的主题在大复兴时期发生了变化。在大复兴之前,宗教改革带来的讲道重点是宣讲上帝的“全备真理”,要么是通过解经式讲道,要么是清教徒采用的更有主题的一种“朴素风格”。
这些风格在大觉醒中得以延续,尤其是在每周的教会聚会中,但大觉醒中另一种布道风格已成为福音派讲道的标志,即只有那些巡回布道者才关注的布道主题:罪、上帝的愤怒、基督的赎罪工作、称义和重生的必要性。这种布道不是为了寻求圣徒的成长,而是更有针对性地让失丧的人归信。
第三,伟大的福音布道家。
第三,大觉醒通过吸引人们对伟大的福音布道家的注意来改变讲道本身。当怀特腓开始他了不起的布道事工时,他在福音派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个有力的、生动的布道家形象,他专门就福音的主题进行布道,没有解经,向四处蜂拥而来的大群人传讲。家庭、教会和社区都因他的讲道而改变。所有这些都催生了一个新的传道人身份:巡回布道家。
并不只有怀特腓而已,其他伟大的传道人也开始了巡回布道——英格兰的约翰·卫斯理、威尔士的豪尔·哈里斯(Howell Harris),以及美洲殖民地的吉尔伯特·坦南特(Gilbert Tennent)、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es)和爱德华兹。很快,传讲福音和呼吁失落之人巡回布道家们遍布了整个新教世界。从那时起,福音派这个标签就和一些主要的巡回布道家联系在了一起:卫斯理、奈特尔顿(Nettleton)、芬尼、穆迪、桑戴(Sunday)和葛培理。

大觉醒将宗教改革提倡的讲道方法转变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完全集中在福音信息上,并由一位杰出的布道家传递。因此,虽然福音派讲道延续了宗教改革的传统,即传讲上帝的话语,但在复兴之后出现的讲道却在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是否是一个负面的变化,导致福音派基督徒注重充满活力的讲道者,从而给宗教改革的遗产带来了断层?它是否导致了牧师和传道人成为兜售掺水版福音的表演艺人?没有!这些担心是对复兴失控的批评,是对好的、真正的奋兴讲道的歪曲。
福音派里总有一些坏苹果,但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而放弃福音派的本质。只要有节制,复兴运动带来的每一个变化都可以被用来改善基督教的事工。讲道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生动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的。以福音为中心的讲道,以及简短的以悔改和信靠基督为结尾的解经式讲道,应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成为平常,因为它们提醒我们福音的基础和我们传福音的责任。而且教会应始终鼓励和支持其有恩赐的传道人。我们可以对大觉醒改变新教讲道的方式表示感谢。
早在福音派兴起之前,改教家们就明白,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他们必须信靠基督。他们的教会、国家或父母的信仰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正如路德所说,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生活在“神的面前”(coram deo),没有人可以代替。
此外,因为改教家们教导我们都有原罪,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然地愿意信靠基督,更不用说过信心生活了。这种转变必须是之后发生的。因此,虽然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大部分都是国教,而且要理问答广泛可及,但后续才出现的“归信主义”(conversionism)种子已经存在。

同样,英国清教徒、荷兰归正会和德国虔诚派都有归信前灵魂争战的神学,这一争战旨在通过使罪人摆脱信靠自己、信靠行为称义的想法,为归信基督做准备。许多人在信主之前经历了一个温和而短暂的属灵不安,而其他人则在发现信仰之路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内疚和自我定罪。
许多人都熟悉路德在信主前与罪疚感的巨大挣扎,但有这一经历的并不只是他。许多清教徒和敬虔派基督徒,如约翰·班扬、约翰·欧文和奥古斯特·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归信福音前都经历了灵魂的黑暗。这种经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年轻的爱德华兹曾短暂地担心他错过了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真正归信之前的“恐惧”。戏剧性的、体验式的归信并不是现代发明,它们在新教历史和神学中有着深厚的根基。
第一,带着强烈情感的归信。
但大觉醒确实强化了标准的福音派归信经历,极度情绪化、戏剧化的归信变得更加突出。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仍然经历了渐进式的归信,因为他们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并由在信徒父母带领下学道,因此悔改和信靠并不一定意味着挣扎。但在第一次大觉醒中,我们看到带着强烈情感的戏剧性归信增加了。
例如,宣教士毕大卫(David Brainerd)在1739年信主之前,经历了一段强烈而持久的属灵困扰:“我以为神的灵已经完全离开了我。……我很沮丧,仿佛天地间没有什么能让我快乐。”然而,在一次祷告中,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可言喻的荣耀似乎打开了我灵魂的视野并给我悟性。……我静静地站着,感到惊叹和赞叹!我知道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没有什么能与神的卓越和美丽相提并论,我所经历到的与之前我对神或神圣事物的所有概念大不相同。
上帝打开了毕大卫属灵的眼睛,使他能够看到耶稣基督面上的上帝荣耀之光(林后4:6)。
安妮·哈塞特(Ann Hasseltine)是一位年轻的马萨诸塞州女性,后来成为一名宣教士。在1807年归信之前,她感到自己“心开始悖逆神”。她认为神没有“权力呼召一个人得救而让另一个人灭亡”。她非常憎恨上帝的圣洁,“我觉得,如果我得蒙允许进入天堂,以我当时的感受,我应该像在地狱一样难受。在这种状态下,我渴望被火销化。”
然而,她后来为了一颗新心而寻求主,并发现了“基督救赎之路的新美”,这使她摆脱了惧怕,并使她走上了舍己服事的生活。像毕大卫和哈塞特这样的故事在大觉醒期间很常见,因为戏剧化的、可回忆的归信成了常态。
第二,归信时间变短。
归信的时间也变得更短。第一次大觉醒中的归信往往需要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因为牧师们要确认归信者是否真实。潜在的归信者也需要时间分辨新心的迹象(对神的爱和其他圣灵的果子),然后才能承认他们的归信是真的。
然而,到了1800年,由于阿米念主义的兴起,归信变得更加取决于个人意志。阿米念主义更加强调人类在救赎上所做的决定。“短归信历程”这一现象也来自“爱德华兹加尔文主义”(Edwardsean Calvinism),爱德华兹认为罪人在意志上有能力选择基督,只是在道德上没有能力,我们可以在爱德华兹的经典著作《论自由意志》(Freedom of the Will)找到他的主张。由于这种强调重心的转变,这让确定归信变成了看意志决定——如承诺跟随基督,而辨认是否有圣灵的果子就没那么有必要了。
我们该如何看待福音派对待归信的这些转变呢?首先,每一种归信的倡导者都同意,从神学上讲,重生是神的一次性工作。经历来自历史、社会和个人因素,人和人都不一样,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自己的改变。
其次,我们不应该把归信时间更短这一转变仅仅解释为阿米念主义或伯拉纠主义的结果。的确,到1800年,阿米念主义在美国越来越流行,而且一些没有受过历史神学训练的福音派基督徒确实用伯拉纠主义术语讲解救恩。但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故事更为复杂:新英格兰加尔文主义者也将“决志”作为他们救恩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毕竟,他们认为,当一个人相信、信靠或将信心放在基督身上时,他就归信了——所有这些都是意志的行为。
归根结底,一个人的意志并不是核心问题,他的意志是不是出于正确的原因才是核心问题。我们如何分辨一个人是出于正确的原因(即对上帝的爱)而不是为自我的好处而归信呢?爱德华兹在《宗教情感》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真正归信的指标不是某种意志,也不是经历某种特定的归信经历。相反,“基督徒的实践”——即谦卑地活出圣灵的果子——才是归信的关键。他写道:“基督徒实践是所有恩典结出的果子中最主要的,既是向别人见证了归信的真诚,也成为对自己良心的证据。”
在宣教上,我们看到16和17世纪的新教基督徒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觉醒的福音派之间的连续性最小。在第一次大觉醒之前,新教基督徒的确也宣教——我想到了新英格兰清教徒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他在马萨诸塞州印第安人中宣教,以及德国的敬虔派——他们向亚洲、非洲和北美派遣宣教士。但更多的时候,改教家的精力都放在了构建一个正统的、敬虔的基督教社会上,他们的使命是针对他们周遭的社会,而不是面向更远的地方。

直到1780年至1830年,我们才看到美国和英国的福音派宣教活动急剧增加。这是威廉·凯利、耶德逊等著名宣教士的时代,也是美部会(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部)、英国伦敦会等伟大差会的时代。
为什么19世纪之前,福音派和新教都没有宣教的兴趣呢?答案很复杂。首先,直到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到了条件成熟的地步,使海外宣教努力能够得到蓬勃发展。到1800年,西欧和美国正处于第一次商业和工业革命大潮中。这些都需要复杂的交通网络,以及西方人士与机构在世界各地许多文化中的存在。
虽然我们批评西方人在剥削世界资源上犯下的巨大罪恶是对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基督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接触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过去他们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历史充满了矛盾和混合的祝福,西方的扩张也是其中之一。其积极的结果之一是,进一步使得福音在全世界传播。
其次,由于第二次大觉醒期间福音派信徒人数增加,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对宣教的财政捐助激增。19世纪初,美国的福音派派基督徒数量急剧增加,这是数以百计的布道家、奋兴家和牧师们不知疲倦地宣扬福音的结果。这些归信者又开始舍己地资助宣教机构,导致福音派宣教活动的增加。
最后,19世纪初,美国和英国的福音派自愿宣教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出于多种原因,美国的福音派信徒还将他们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教会以外的事工中:孤儿院、扶贫、禁酒、圣经出版以及国内外宣教。
简而言之,这些历史现实——现有的交通网络、西方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存在以及愿意为福音事业奉献时间和资源的福音派——极大地扩大了19世纪宣教活动。这反过来又开启了伟大的宣教世纪。
在过去的200年里,世界变小了很多。尽管我们有很多问题,但福音派还是成功地将福音带到了更远的地方。正如我在这里试图论证的那样,通过大复兴,新教过渡到了福音派,这总的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过渡。总的来说,这一过程使我们长进,使我们能够做最关心的事情:传讲圣道,引导罪人归向基督,并调动我们的资源将福音传到地极。
只要我们对现代性、不忠和世俗保持警惕,并致力于通过福音事工高举基督,我们就会在上帝的祝福下,在即将到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继续前进。谁知道呢?神可能在这中间带来另一次大觉醒。毕竟,祂“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弗3:20)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Revival Turned Protestants into Evangelic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