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读到关于苏格兰基督教的情况,这个国家的属灵事实会让你回想起大学青年团契的某个女孩——那个积极参加所有查经聚会的女孩,那个曾经计划投身海外宣教的女孩。但现在,你读到关于她的动态时会感到吃惊——她已经解构了她的信仰,比你想象的更彻底、更迅速。
她的转折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你可能会打电话给朋友,希望有人可以帮助你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这甚至可能让你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一些怀疑。
在过去,苏格兰的基督教——尤其是她对改革宗神学的坚持——一直非常坚强。苏格兰政府和教会都深受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的影响,而诺克斯又深受加尔文的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苏格兰约有一半的人口都是教会成员(而且苏格兰几乎所有教会都是长老会)。
在阿伯丁市(Aberdeen),有95座教堂为当地18万人提供服务。1965年,还是大学生来这里进修的辛克莱·傅格森(Sinclair Ferguson)称其为“一座尖顶之城”。
他说:“这座城市看起来像现代的基督教雅典。到处都有教堂——也就是礼拜场所,教堂无处不在。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教堂都是由这种特别坚固、强大、几乎压倒一切的花岗岩构成。它们看起来真的很宏伟。”
苏格兰教会拥有一切:良好的神学遗产、高教会出席率和坚固的建筑。它还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毫不干预。但是,如果你知道从哪里观察苏格兰教会,你会发现裂缝已经开始显现。傅格森说,虽然教会成员众多,但奉献却“很糟糕”。
不久之后,苏格兰的基督教就走向了崩溃。在60年里,苏格兰教会成员从130万骤降至30万,同时声称没有宗教信仰的苏格兰人的比例已经上升到近60%。
阿伯丁现在是苏格兰最世俗的城市,而苏格兰又是联合王国最世俗的成员。巨大的花岗岩教堂建筑成了餐厅、公寓,以及名字和“灵魂”一词有关的酒吧。几年前,一位记录这种转变的摄影师称之为“耶稣已经离开了教堂”("Jesus Has Left the Building")。

在阿伯丁市中心的皇后街,靠近警察局、市议会办公室和当地媒体机构之地,坐落着该市最大的教堂建筑之一。四年前,它被卖掉了——但这回不是卖给一家夜总会或零售店,而是卖给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
十多年前,三一教会(Trinity Church)已经脱离了苏格兰国教。在此后的几年里,她传扬福音、开始了学生事工,并有了一些发展。对于这座巨大的建筑来说,这间教会太小了,但当这间教会的成员们看着这个空间时,他们看到了可能性和盼望。
傅格森也是如此。他说:“若主许可,它将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真正的灯塔。”
这些并不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傅格森已经在阿伯丁买了房子。虽然已经退休,但这位有影响力的现代改革宗牧师-神学家将把他的主要时间花在苏格兰最世俗的马路边教会的晚堂讲道上。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春天的标志,”他说。“谁知道教会将看到什么样的收成?会是30倍吗?60倍?还是100倍?那是神的事,也是祂的特权。但这个春天的迹象鼓励我们继续播种。”
最早在皇后街建造教堂的那间教会比三一教会早了大约165年离开苏格兰国教。他们的牧师约翰·慕里(John Murray)反对让拥有土地的贵族(这些贵族不都是基督徒)决定这间地方教会的神职人员。他并不是唯一的反对者。在苏格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教会分裂中,1200名牧师中有474人退出了苏格兰国教,并于1843年成立了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
慕里带领的这间教会后来被命名为北区教会(the North Church),在一连串有影响力又有恩赐的福音派牧师带领下,他们不断壮大。到19世纪60年代初,该教会是“整个城市的福音中心”,教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加米(Alexander Gammie)报告说。当这个宗派想开始向“城市的南部”拓展时,北区教会是带领这场植堂的不二人选。
会众“一致热情地决定采用这一计划”,加米在1909年写道。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们需要更多空间,因此他们建造了一座18500平方英尺的五层楼房。他们用传福音活动、诗班和管弦乐队来填充它。他们每周日举行九次不同的聚会,然后在一周内再举行26次。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这个“工业蜂巢”周围嗡嗡作响。加米写道,他们做工的果效很明显,以至于“许多参访者从全国其他地方赶来观看这个事工的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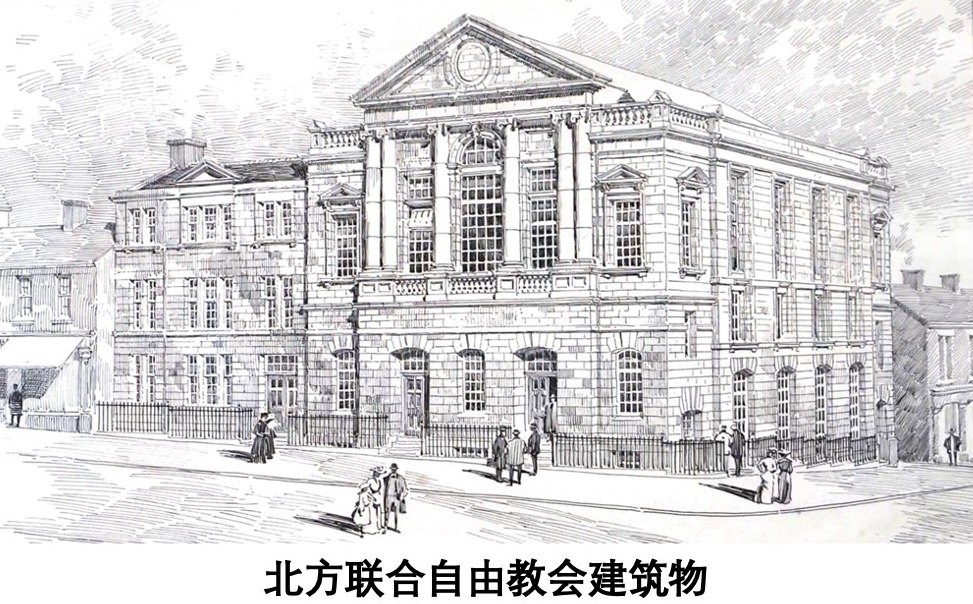
当时堪称苏格兰教会的全盛时期,在那个时候,苏格兰是一个坚定地信奉改革宗神学的基督教国家,这个状态持续了大约有350年。教义如此坚实,以至于很少有教会因为神学而分裂。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谁可以任命牧师——是会众还是上帝设立的政府。(也许你注意到查尔斯国王最近宣誓要维护苏格兰教会的独立。而且,尽管他是英格兰教会的官方元首,但他的这一地位并不延伸到苏格兰教会。这两件事都不是偶然的。)
然而,当时也是牧师和神学家开始建议以新的方式来看待圣经的日子。这些神学家们说,圣经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没有关系。创世故事可能是巴比伦神话,亚伯拉罕实际上并不存在,挪亚时期的洪水几乎肯定没有发生,也不存在吞掉约拿的鱼。实际上这些神学家认为,《旧约》显示了人类的宗教演变,表明人类如何摆脱了那些原始的信仰。
“到了历史的这一刻,基督徒的基本问题是:‘上帝的话语说了什么?’”真理旌旗(Banner of Truth)出版社的编辑伊恩·默里写道。“新的问题变成了:《圣经》中有多少是神的话语?”
下一个问题很自然地成了:“那基督呢?他所说的有多少是真的?”
教会“失去了信心,迷失了方向。”教会长老西蒙·巴克(Simon Barker)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他看到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在持续发生。教会“突然为基督感到羞愧,认为教会不可能指望人们相信复活的救主。因此,带着一种启蒙的态度,相当尴尬地盯着自己的脚,停止教导教义,开始说:好吧,只要我们对邻舍和善,经常和邻舍打球,我们就会有好见证。”
1929年,当曾经脱离国教的苏格兰自由教会中大部分决定重新回归苏格兰国教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声明——上帝的话语“包含”在圣经中。宣扬圣经有谬误的神学家没有一个受到惩戒。
当傅格森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神学学位时,他的教授中只有一两位是传统福音派人士。福音派的学生俱乐部规模很小,他们开玩笑说他们可以在电话亭里开会。
然而,四百年来的优秀神学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与教会有关,”傅格森说,尽管他的父母没有参加任何聚会,但他每周都去上主日学。在国家开办的学校里,他记住了十诫、主祷文和天国八福。教会的礼拜有电视转播,双层巴士会带着孩子们参加主日学野餐,全国媒体会广泛报道每年的大会。
但奉献开始下降。你可以在《苏格兰教会年鉴》中查到,该年鉴将苏格兰每个教会的人数和年奉献额放在一个表格里进行统计。
傅格森说:“当我在大学图书馆时,我无意中听到一位牧师和学院图书馆管理员之间的对话。那位牧师说,‘你看到斯蒂尔先生(Mr. Still)所在教会的惊人奉献了吗?”
傅格森的耳朵听到了这句话——他是斯蒂尔通过解经式讲道和对主的爱所振兴教会的一部分。(想听更多关于这个故事的内容,请听傅格森的音频故事。)
“图书管理员说,‘哦,是的,虽然他的教会里都是学生。’”傅格森回忆说。那位图书管理员的回答似乎没有解释教会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奉献收入。“学生没有很多钱,”他想,“那是胡说八道。”
人们不奉献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去教会。尽管在1957年约有60%的苏格兰人是教会成员,但每周去教会的人不到20%。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长的教会成员名单掩盖了这个问题。这也扼杀了传福音的动力。
“这让我们这些福音的执事感到满意,好像我们在苏格兰的传福音责任已经完成一半了。”汤姆·艾伦(Tom Allan)写道,他是1955年葛培理苏格兰布道会的执行主席。
一些笃信圣经的基督徒采取了行动——为期六周的葛培理布道会让数千人接受了基督。20世纪70年代初,威廉·斯蒂尔开始邀请牧师们参加聚会。这一活动后来发展到每年几百名福音派牧师——这是苏格兰国教大会之外最大的会议。在傅格森的校园团契小组中,任何不解经的人都不会再来了。更多的人进入牧师行列,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而是因为他们感到了蒙召。
傅格森说:“这增加了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事的感觉。风就在我们背后。”
傅格森说,虽然有福音派牧师和一些福音派教会成员,但他们即使在自己的会众中也通常是少数。因为“除非福音以社区为基础,否则无法保证其未来。”
也没有什么架构来支持他们。他说:“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创建了一些机构。我不是贬义的意思,而是一种称赞。福音派机构让福音派信念得到了制度化的保存,这样就可以传递下去、服事未来。”
在苏格兰,人们不会如此迅速或轻易地撰写一份声明或创建一个非营利组织。
他说:“(苏格兰福音派领袖们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策略——基本上就是没有策略。他们常用的说法是‘悄悄渗透’。”
在一间教会里,一个保守的牧师有时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宗派层面而言,这样做并不奏效。相反,温和的中间派——即便他们都是相信耶稣的人——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在一个自由化的文化中,这一策略的结果就是自由化。
傅格森说,“悄悄渗透的危险在于,最后是自己被悄悄渗透了。”
这就是由高举科学、理性的文化所滋养的圣经有谬误这一涓涓细流如何能发展成了溪流。这就是在一个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这种文化滋养下,在圣经无误上妥协的小溪如何最后变成了大河。
渐渐地,这种运动可以冲垮一个教会的根基——一个400年来坚持以改革宗神学为基础的厚实根基。
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个时候,教会垮了。
牧师大卫·兰德尔(David Randall)在2015年写道:“多年来,教会的衰落被归咎于‘枯枝落下’,即那些成为教会成员却没有对基督作出任何真正承诺的人离开了教会。他们的离开让教会变得更结实、更健康的教会,这一想法一度让我们感到安慰。”
这种安慰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苏格兰的教会成员人数没有出现反弹、上涨,甚至也没有减缓直线下降的趋势。
官方的说法是,教会因苏格兰的出生率下降或教会未能接触到年轻一代而受到影响,更好的技术使用或更多的自由化可能会有所帮助。自2009年以来,苏格兰国教一次又一次地投票,以扩大对同性关系的认同。
这些投票非但没有吸引教会以外的人来到教会,反而只是加速了保守派牧师候选人、牧师和教会的出走。
其中一个是阿伯丁北侧的希尔顿高地教会(High Church, Hilton)。
90年代中期,彼得·迪克森(Peter Dickson)悄悄地在希尔顿高地开始了福音派事工。
大卫·吉布森(David Gibson)说,“他有效地在一个濒临死亡的教会中植入了福音,”大卫后来成了彼得的助理牧师。“他们没有聆听圣经教导的基础,所以迪克森从10分钟的讲道开始。”
每隔一段时间,迪克森就会延长讲道时间,直到最后达到30分钟。
吉布森说:“他用解经式讲道喂养着教会中的男女,爱他们,以及通过使自己的家成为一个欢迎和关怀的地方而得到改变。他慢慢地提高了教会生活中的属灵温度。”
西蒙·巴克是长老议会的一员,他说:“我不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真的信主,因此看着他们真正信主是一种谦卑下来的经历,”他说。“我经历这种谦卑好几次。”
在迪克森服事大约15年后,同一个长老区会下面的另一间教会呼召了一位离开妻子和女儿参与同性关系的男士担任牧师。迪克森和其他11位牧师表示反对,在当地长老区会和后来的全国总会上争论不休,并最终失败。
经过三年的“谈判、讨论、教会法庭、决策和通信”,苏格兰国教决定差派一位长老前来“评估”和帮助治理希尔顿高地教会。对此,迪克森的回应则是离开了国教。
“15年前,没有人会和他一起离开,”吉布森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会众已经定期听到福音多年了。在200多名成员中,有170人随他而去。
他们是第一个因苏格兰国教在同性议题上的立场而离开该宗派的教徒。
巴克说:“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他一直都是苏格兰长老会(国教)的一员。把福音放在你的宗派委身之前,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个离开的人,这是非常痛苦和疲惫的。
“我们为之哭泣,”他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从来不想分开——那会向世界发出什么样的信息?这并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出走的这个团体自称“三一教会”,并开始在一个褪色的艺术装饰酒店宴会厅聚会,在那里你有时可以找到派对的残留物,或闻到前一天晚上的酒味。
巴克说:“这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让我们知道不要依赖建筑物。但它也教会了我们,没有建筑物的教会运作是多么的有限。”
“三一教会”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无法租到场地,因为大型派对预定了所有的场地。没有固定的地方,也就意味着他们很难邀请朋友参加聚会,也很难开始邻里事工。而且他们总是意识到,某些讲道片段一旦得到病毒式传播,就会让他们失去场地。

这种无根的感觉因为加入了国际长老会(IPC)作为他们的新长老会家园而变得更加复杂。IPC由薛华(Francis Schaeffer)创立——想想看,应当带来很多好的对话、很多好的团契,而且近年来在英国和欧洲有令人兴奋的教会植堂活动。这里有对认信的委身和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生活。但关系是新的,需要时间来深入发展。
迪克森和吉布森不断地需要讲道,一个星期天接着一个星期天。最后,迪克森转而带领苏格兰大学和学院基督教团契(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ship)的学生事工,而吉布森则开始担任三一教会的主任牧师。
吉布森说:“彼得在希尔顿和三一的事工所付出的代价和非同寻常的忠心,以及他的长期成果,是我所看到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
慢慢地,三一教会继续成长。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建筑筹集资金。在一次IPC会议上,吉布森认识了辛克莱·傅格森,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改革宗神学家之一。
傅格森也因此认识了大卫·吉布森。
“上帝给了大卫一个巨大的决心,”傅格森说。“他智识超群,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解经者。他对会众有一种真正的爱。而且与他的长老们一起,他们有一种真正的热情,即他们可以在这个城市创造一些东西。”
还记得1843年离开苏格兰国教的教会吗——由约翰·慕理带领的教会?那个有如此多的聚会、事工和志愿者的教会,以至于当时许多观察家称这间教会是一个“蜂巢”。
在最近的100年里,这个蜂巢几乎是空的。只有30名年纪老迈的成员在庞大的建筑里缓慢移动,这座建筑物拥有一个能容纳1000人的主堂,另外两个大厅、多个教室,以及让管理员居住的三居室公寓。

1929年,该教会重新加入了苏格兰国教,随后就面临着人数下滑,虽然该教会在成员人数减少的情况下一直在有效地整合资源。
因此,日渐萎缩的前北区联合自由教会在2004年与附近的教会合并,并在2017年再次合并。甚至在苏格兰国教正式批准同性婚姻之前,该教会就“决定放弃苏格兰教会在人类性行为方面的传统立场,以实现包容性”——这段话引自教会网站上的自我介绍。
然而,因为人数太少,到了今年5月,苏格兰国教宣布它将在未来5年内关闭这间教会。
就在三一教会有足够的资金认真考虑购买会址的时候,北区教会的这座老建筑进入了房地产市场。由于该建筑仍然属于会众——因为1929年的文书工作出了错——三一教会可以在不需要苏格兰国教介入的情况下购买它。
“我记得当时有点怕,因为它太大了,而且里面有很多房间,”巴克说。它也需要许多更新和维修。屋顶漏水、电力系统需要大修,每个房间都需要进行一些改造。
“你们可能只想买一部分,”卖家代表建议三一教会的长老们。
但他们越看越兴奋。
吉布森说:“它好像呼吁我们让它成为位于市中心的一个福音中心。他可以想象着在这里为企业高管提供福音午餐会,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或庇护所的事工,以及在管理员公寓里安置教牧实习生。”
这是一个美丽的愿景。但这将需要大量的工作,如果能得到一些帮助就更好了。
写了50多本书,在几乎所有的改革宗大会上讲道,在几乎所有的改革宗神学院任过教,以及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历史悠久的教会担任过牧师……这是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履历,傅格森于2013年退休。
除了为他的继任者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带领腾出空间外,他没有其他的退休安排,因此回到了苏格兰的家。他在女儿的教会帮助了一段时间。当她的牧师在2019年搬到澳大利亚时,傅格森知道他想给新的主任牧师一些喘息空间。
在IPC的一次活动中,他提到了自己目前的安排。
吉布森听到了。他回家后写了一封信,邀请傅格森加入三一教会在阿伯丁的工作。
18个月过去了,吉布森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新冠疫情来了,三一教会的聚会转移到了网上,他们变得更忙了。
“然后有一天,我在一家超市里,他打电话来,”吉布森说。傅格森当时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如果他不去做牧师的话,职业高尔夫是他可能采取的路线。)
“我很感兴趣,”傅格森告诉吉布森。“我们来谈一谈。”
傅格森很好奇,就提出想要来看看这座教堂,在疫情期间,三一教会曾使用过这座教堂,但在修复之前又搬了出来。傅格森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他感到“目瞪口呆”,他说:“这座教堂很有潜力。”他知道教会不是建筑物,但他喜欢在阿伯丁的中心地带建立一个繁荣、活跃、热闹的强大神学和事工中心这一想法。
傅格森说:“就像一本书的封面一样,建筑物确实能说明一些问题。如果上帝赐予供应,并且(三一)实现了它,那么它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表明这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在其他教会关闭的时候,这个教会却在扩张?’”
即使你所在的教会信仰告白是约翰·诺克斯写的,即便教会的神学扎根于《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即便你的建筑是由花岗岩制成的,如果没有福音,你的教会仍然会失败。
巴克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基督教的精神几乎消失了。那些在我们之前的人忠心耿耿地服事,建立了教会,而我们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挥霍了它。这是很可怕的。”
傅格森说:“那些曾为福音提供最大机会的地方,当他们不再需要福音时,就会变成非常艰难的地方。几年后,阿伯丁的市中心将只有四个苏格兰国教教会。”

吉布森说:“在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活生生的福音见证。三一教会的这座建筑物正好位于该市的市民、经济和司法中心——街边有商业,拐角处有法院,隔壁是城市规划的商店和广场。阿伯丁大学也在步行范围内。”
这个位置很适合建立教会。但植堂必须尽快发生,吉布森说:
“如果三一的事工有任何成果,那都是来自于之前几年流泪播种的东西。我们经常使用‘植堂’这种机构化语言,但很少注意到基本的种子原则,即种子埋进土里死了,植物才能长出来。彼得的忠心和带领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带领我们进入新的领域,我们在其中耕耘和播种。而三一教会现在只是想继续进行同样昂贵的事工。已经有很多人死去了!……我不认为任何做这些事的人从未质疑过——这值得吗?但我们相信它是值得的,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尝到了死在地里的种子带来的果实。”
在招募傅格森的同时,吉布森一直在讲道,希望更多的奉献者可以为教堂重修工程捐款,并帮助计划苏格兰版的查尔斯·西缅释经工作坊。到明年9月,一个小型的牧师联盟将提供课程,包括解经原则、叙事文讲道和福音事工方法论。他们将在三一教堂的新空间里举行会议。
像他之前的那些人一样,吉布森想把福音传到未来。而且他想在从过去的改革宗基督徒那里得到的建筑中做到这一点。
“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巨大盼望的标志,”傅格森说。“有这些春天的迹象。你知道,主不需要给我们这些春天的迹象,但他就是给了。而三一教会肯定是其中之一。”
编注:要了解辛克莱·傅格森的更多故事,请听“为什么辛克莱·傅格森搬回苏格兰最世俗的城市”播客,想了解更多关于三一教堂和阿伯丁的情况,不要错过这个10分钟视频。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Jesus Has Left the Building': Scotland's Secular Slide—and Signs of H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