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黑格尔借这句话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尤其是理解历史的智慧,往往要等到尘埃落定,我们有时间回头审视时才会浮现。
在事件发生的当下,要判断其历史意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被自己的情绪、希望和恐惧所束缚,受限于对事态的有限认知,受制于掌权者对叙事的强大影响力,也无从知晓未来的后果——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形成深思熟虑的判断。因此,人们喜欢引用前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名言。1972 年,当有人问他对四年前法国五月风暴的评价时,他只淡淡回答:“现在下结论还太早。”确实如此。冷静的思考,往往胜过仓促的评论。
也因为这个原因,过去一年出版的两本书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它们分别尝试从不同角度解读 2020 年夏天在西方民主国家达到高峰的那场社会与文化动荡。(对这场动荡的称呼本身就带着强烈的立场。根据说话人的身份与态度,有的称它为“社会正义”或“反种族主义”,有的称之为“身份政治”或“取消文化”,还有人称它为“种族清算”“交叉性”或“大觉醒”(Great Awokening)等。)
《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
穆萨·加尔比(Musa al-Gharbi)著
从理论上看,我们的社会似乎比以往更加强调平等:偏见成了禁忌,多元文化备受推崇。然而现实中,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却不断加剧。
在《我们从未觉醒》中,穆萨·加尔比指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密切相关,且都与一种新精英的崛起有关——他称之为“符号资本家”。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432 页。
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的《我们不满的夏天:确定性的时代与话语的消亡》(Summer of Our Discontent: The Age of Certainty and the Demise of Discourse)是一部结合历史与新闻写作的作品,从 2008 年讲到 2024 年,重点围绕 2020 年针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的社会反应展开。而穆萨·加尔比(Musa al-Gharbi)的《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则采取社会学与理论的路径,运用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的既有分析范式,来为其大胆的论点辩护。
这两本书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二者都由著名出版社(克诺夫〔Knopf〕与普林斯顿)出版,装帧精良、研究扎实,也都有一批你意料之中的知名人物撰写推荐语: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泰勒·科恩(Tyler Cowen)、尤瓦尔·列文(Yuval Levin)。两本书文字敞亮、可读性强,目标读者是那些思考严谨但并非专业学者的普通读者。作者都对他们所分析的社会发展提出批评,但更渴望理解,而非只停留在谴责层面。更重要的是,这两位作者都是四十岁出头的有色人种男性,对右翼民粹主义保持尖锐批判,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种族反扑”的一部分。两本书都十分杰出:深刻、好读、富有挑战性并具有启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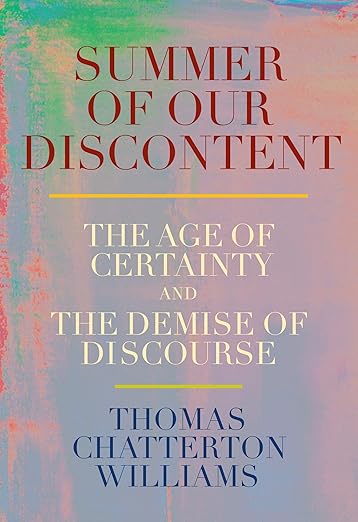 《我们不满的夏天》从 2020 年 5 月 25 日弗洛伊德遇害那天写起。那一幕几乎已烙印在世人心中:一名白人警察以膝压颈的方式压制一名黑人男子长达九分半钟,直到他窒息而亡,而这一切被拍摄下来,瞬间在全世界传播。然而,威廉姆斯给出了一个不同且重要的视角。他指出:“乔治·弗洛伊德是个穷人。这是他生命中最显著的事实”(第 xiv 页)。“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不必、也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种族……他的死亡与他的贫困状况密切相关。他因此丧命,是因为一张大多数黑人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的假钞”(77 页)。
《我们不满的夏天》从 2020 年 5 月 25 日弗洛伊德遇害那天写起。那一幕几乎已烙印在世人心中:一名白人警察以膝压颈的方式压制一名黑人男子长达九分半钟,直到他窒息而亡,而这一切被拍摄下来,瞬间在全世界传播。然而,威廉姆斯给出了一个不同且重要的视角。他指出:“乔治·弗洛伊德是个穷人。这是他生命中最显著的事实”(第 xiv 页)。“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不必、也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种族……他的死亡与他的贫困状况密切相关。他因此丧命,是因为一张大多数黑人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的假钞”(77 页)。
威廉姆斯进一步主张,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弗洛伊德”:一个是真实而复杂的弗洛伊德;另一个则是简化后、成为社会象征的弗洛伊德。“一方面,他是某人的儿子和兄弟,在那个长周末过得很艰难,无业,体内含有甲基安非他命和芬太尼……在车里打盹,几分钟前刚用假钞买东西”(第 4 页)。“另一方面,则是被永恒化的弗洛伊德,他的死亡定格在影像里,在我们脑海中不断循环播放……那是多年来一直酝酿着的、关于黑人刻骨之痛与白人至上主义沉重枷锁的观念。”(第 5 页)
在他悲剧的时刻过去短短几分钟,前者便几乎完全被后者吞没。数小时之内,人们便以近乎基督受难的方式来感受和理解他的死:
难道弗洛伊德不是以一种直观可见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脖颈和肩膀承受了他所在社会的种族罪孽那可怕的重负吗?而那重负,就是我们所有人罪孽的总和,难道没有反过来压垮他吗?有一个人为我们死在那肮脏的人行道上,他没有问‘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而是令人心碎地呼唤他的母亲。那位迟钝的行刑者……仿佛洗净了自己的双手,将它们深深插进口袋”(第 7 页)。
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爆发了数千起抗议活动,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这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威廉姆斯通过讲述西方世界自 2008 年以来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并突出了四个关键因素。
在威廉姆斯的叙述中,能全身而退的公众人物寥寥无几。正如我们所料,他对特朗普的批评毫不留情。从他在任期间普遍的谎言与无知,到具体建议用光疗法治疗新冠肺炎甚至向人体注射消毒水等荒谬言行。
但威廉姆斯在许多方面对进步派左翼当时应对措施的抨击更为激烈。“在短短两周内,我们几乎未加深思熟虑地,就从谴责人们上街游行,转向谴责他们不上街游行,”他写道。这种思想上的混乱,至今仍在让我们付出代价。
威廉姆斯特别关注 2020 年盛行的“反种族主义崇拜”——从罗宾·迪安杰洛(Robin DiAngelo)、伊布拉姆·X. 肯迪(Ibram X. Kendi)和尼科尔·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的理论建构,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机构性忏悔、明尼阿波利斯市削减警局预算、《纽约时报》的强制辞职、波特兰的表演性反种族主义等现实后果——这一切在八月的基诺沙事件中达到高潮:在雅各布·布莱克(Jacob Blake)遭枪击后,CNN曾因其将现场描述为"激烈但基本和平的抗议"而臭名远扬。
威廉姆斯随后将我们带入当下,通过章节探讨了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潮通过社交媒体的全球输出、取消文化、一月六日国会山事件,以及 2023 年 10 月以来的以色列与加沙冲突。威廉姆斯轻而易举地表明,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都被 2020 年那个带着强烈种族颜色的夏天深深影响了。
《我们不满的夏日》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威廉姆斯的叙事功力很强,善于在熟悉的事件中穿插不为人知的细节;他文笔流畅,时而闪现智慧火花;恰到好处的幽默多少冲淡了那段历史所带来的阴郁与不快回忆。
然而,本书最缺失的正是盼望:盼望这段令人不适的故事不仅是集体性的灾难记载,盼望现状已经或即将改善,希望我们确实从过往中汲取了教训。(不过平心而论,对于标题带着“不满”、副标题写着“消亡”的著作,我们本就不该期待它会有昂扬的基调。)
有些读者会发现在一位从容的叙述者引领下重温那个夏天,能带来某种释然,毕竟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安然无恙。我自己就是如此。但也有些人可能会渴望更多:一些积极的迹象、一条前路、某个令人鼓舞的案例,或某种大胆的新提议。对他们来说,这本书恐怕无法满足这些期待。
《我们从未觉醒》里处处可见大胆的论断。当西方世界普遍认为自身在 2010 年代至 2020 年代初经历了“大觉醒运动”——无论人们对此欢欣鼓舞还是痛心疾首——穆萨·阿尔加比却以冷静而坚定的态度回应道:不,事实并非如此。
有些人假装自己觉醒了,也有些人真心以为自己觉醒了;另一边,则有人猛烈批评、甚至嘲笑“觉醒”及其追随者。但在加尔比看来,那场所谓的“大觉醒”根本就没有发生:
我们中有些人假装经历了一场觉醒的过程,或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觉醒。另一些人则猛烈批判或嘲讽这场觉醒及其所有追随者。但实际上,那场所谓的“大觉醒”根本就没有发生:
简而言之,问题不在于“符号资本家”过于觉醒,而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觉醒……这些符号资本家经常做的事,反而是在利用、延续、加剧、巩固、甚至掩盖各种不平等,而且往往伤害的正是他们口口声声要替之发声的人。我们对社会正义的真诚承诺,却为这些行为披上了一层本不配拥有、且极具误导性的道德外衣。(第 20 页)
为了论证这一点,加尔比引入了几项社会学术语,其中最重要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我们在社会层级中因声望、认可、荣耀与地位而拥有(或不拥有)的各种资源。这种资本可能来自我们在某组织中的职位、信誉、经验或别人对我们的信任;也可能来自学历、阅读、学位、毕业院校、专业权威;或是文化性的,如语言、穿着、举止、品味、观点、术语等等。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觉醒已成为当代精英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本”(第 26 页)。文化精英之间辨识彼此地位、并展示自身地位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们在种族、性、性别、残障、身份认同等议题上的立场,以及他们表达这些立场所使用的语言。
在文明社会里,以特定术语表达的进步观点,通常被视为高地位的象征。然而,这些观点通常对他们声称代表的人群几乎没带来实际好处;反而常常成为自我服务、自我巩固地位的手段。正因如此:“符号资本家与他们主导的机构,其表面上的觉醒程度可能远高于实际情况”(第 36 页)。
这种表象与现实脱节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性别议题上:许多人公开高喊“跨性别女性就是女性”,但在现实中,当涉及约会或婚姻选择时,他们的行为并不反映这一信念。在经济议题上: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似是一场草根反不平等抗争,但主要参与者其实是报酬优厚、从全球化中获利的高学历“符号经济”从业者。在种族议题上:近年来企业和大学推行的“多元、公平、包容”(DEI)计划,获益最大的不是底层员工或弱势学生,而是那些担任“社会正义铁饭碗”(social justice sinecures)职位的专业人士(107–110 页)。
环境政策方面,美国那些最进步的都市区,新建住房反而更少,警务执法更为严苛,不平等现象也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婚恋观念上,对传统家庭抨击最猛烈的人,往往自己恰恰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并且最终组建的也是类似的传统家庭。慈善捐助层面,富裕的进步派人士将其收入用于慈善的比例,低于受宗教动机驱动的郊区及乡村保守派,而且他们的捐赠更少流向贫困社区。
无论你看向何处,符号资本家们都在声称代表贫困和边缘群体发声,而实际受益的大多是他们自己的荷包。因此,“非精英阶层最好忽略符号资本家们的言论,转而观察他们的实际行为。”
话虽如此,《我们从未觉醒》并不是对进步主义的猛烈抨击。书中虽揭露了大量故作姿态和虚伪行径,尤其在关于图腾式资本主义和受害者竞相比惨的那章中,但阿尔-加尔比并未陷入党派之争的咆哮,他更倾向于选择解释,而不是谩骂。
例如,他坦然承认自己也是符号资本家阶层的一员,并意识到反觉醒阵营与觉醒阵营同样热衷于标榜姿态和符号表演。他梳理了过去百年间四次"觉醒浪潮"的相似之处,通过突出其间的多重对应关系,证明了过去十年的变化其实并不算前所未有。
更重要的是,他将表演性的觉醒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认真对待并探寻其根源。他先是阐释“精英过剩”现象(99–103 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于可提供给他们的高位工作,会因此产生怨气,又进一步分析了“创意阶层”的兴起(134–146 页),然后讨论了“奢侈信念”(用来彰显精英身份,却往往伤害穷人)与“道德许可”(持有某些观点能当作防止被指责为种族主义的护身符),并将这些现象串联成连贯的整体(270–295 页)。
全书笔调细腻审慎,论证均以实证研究和量化数据为支撑,并附有长达百页的参考文献。
然而他的论述始终清晰明了,不拖泥带水,也不闪烁其词。关于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这段论述就是个绝佳范例:
被反对者贴上“批判性种族理论”标签的这套思想体系,显然不是弱势阶层和受压迫者的语言。它不属于贫民区、拖车公园、衰败郊区、后工业城镇或全球贫民窟。恰恰相反,这些思想主要受到高学历且相对富裕的白人群体青睐,其中混杂着心理学与医学的治疗性话语、记者与活动家的干预主义、法律与官僚体系的繁琐技术性表述,以及现代人文学科中伪激进的诺斯替主义。这完完全全就是符号资本家的专属话语。(274 页)
严谨的研究、清晰的文笔与紧凑的论证贯穿全书,是一本赏心悦目的好书。
威廉姆斯和阿尔-加尔比都未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目的在于描述现状而非开出药方,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相较而言,阿尔-加尔比更接近于指明前进方向,或者说提供了我先前所说的那种希望。
部分原因与两本书的结尾氛围有关。《我们不满的夏天》的后记谈到 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及其后续,让人感觉世界似乎被困在永无止境的厄运循环里;而《我们从未觉醒》的结语则提出了一些未来可以继续探讨的方向,使人隐约看见可能性。这种差异也与时间尺度有关:威廉姆斯讲述的是十五年间的故事,阿尔-加尔比描绘的则是百年周期,最近这轮动荡仅是其中一例。这种长镜头能为作者与读者都提供急需的视角,让我们更冷静地看待过去的动荡十年。
在我看来,另一重差异源于隐含的人性观。《我们不满的夏日》描述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以我们之名上演的事件,作为读者的我们至多只是旁观者,在华盛顿、明尼阿波利斯或纽约时报大楼发生的荒诞情节面前摇头叹息,我们被动目睹事态发展,能做的微乎其微。
相反,《我们从未觉醒》的核心主角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阿尔-加尔比笔下的符号资本家——否则也不会阅读这样的著作。稍加反思便会发现,书中描绘的诸多虚伪、地位博弈与道德矛盾,正是我们自身的写照。正因为作者与读者身处同一困境,我们才能内化并反思阿尔-加尔比隐含的诘问:我们在哪些地方把行动主义变成了表演?我们的道德逻辑在哪些地方变得自利?我们究竟有没有把自己所宣称的理想落实在与身边有需要之人的真实关系里?他们是谁?我们是否谨慎,不让自己的义行成为表演?还是我们已经“得了该得的赏赐”?
历经五年沉淀,人们普遍意识到 2020 年那场社会激荡走得太远了。疫情过后,从觉醒资本主义、取消文化到无意识偏见培训和跨性别权利,诸多议题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与社交媒体氛围已发生深刻转变。
但从另一面来看,这场变革又远远不够。许多种族不公依旧原地踏步;许多改革只是表面功夫,结果反而让更富裕、更受教育、更特权的群体受益;许多弱势者依然在等待真正的觉醒降临;许多教会在 2025 年依旧保持着 2019 年的那种泾渭分明的状态。
这两本书都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尤其是阿尔-加尔比的著作——能够通过重构那个动荡年代的叙事框架,挑战我们的认知并带来新知。前提是,我们需以谦卑之心(“主啊,是我吗?”)而非自义之心(“感谢主,我不像那个符号资本家”)来品读。时代思潮屡经变迁,未来仍将如此。对过往冷静深刻的思考,终将帮助我们在下一次浪潮中做出智慧的回应。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ave We Ever Been W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