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J. D. 万斯的这本《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出现在纽约时报夏天畅销书榜单上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之所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因为我以为这肯定是“那种书”,那种进一步强化对阿巴拉契亚地区美国人刻板印象的书,在那些书里——借用作者的语言——当地人就好像没有牙齿、近亲繁殖的白痴一样。
像一个典型的乡下人一样,我对那些把我的家乡当作无知、种族主义、无可救药地陷在上世纪扭曲时光中的外乡人很警惕。我在佐治亚州东北部的丘陵和凹地("hollers")长大,在一个小镇上,上帝和国家——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地理解这两个词——都是社会-政治上保守主义的同义词。
我的亲戚们都是在建筑工地和农场工作的朴实人。他们在杂货店里宰肉、在大风暴后修理电线,也在当地学校教书,照顾着拥有昂贵住宅的“外来人”家门口的草坪。他们听着乔治·琼斯(George Jones)的歌,去沃尔玛购物。
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获得通过后,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我家的生意也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中受到重创。我的族人和万斯的族人一样,都是“红脖子”、蓝领工人、白人中产阶级——这群人是美国重要的宗教和投票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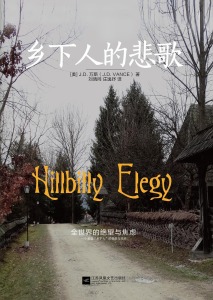 但是打开书后才翻了不到两页,作者就打消了我对刻板印象的顾虑。万斯的悲歌(也就是一首哀歌)透过他作为一个阿巴拉契亚人的经历来审视我们这个严重分裂的国家。“美国有一个问题,”他写道,“我的主要目的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当你出生时脖子上就挂着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当万斯娓娓道来他艰辛的个人叙事时,我听得津津有味:从肯塔基州东南部山区的生活,到俄亥俄州米德尔镇的铁锈带,他的家人搬到那里是为了从事某个行业,这行业最终离开了小镇,留下了失业和痛苦。
但是打开书后才翻了不到两页,作者就打消了我对刻板印象的顾虑。万斯的悲歌(也就是一首哀歌)透过他作为一个阿巴拉契亚人的经历来审视我们这个严重分裂的国家。“美国有一个问题,”他写道,“我的主要目的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当你出生时脖子上就挂着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当万斯娓娓道来他艰辛的个人叙事时,我听得津津有味:从肯塔基州东南部山区的生活,到俄亥俄州米德尔镇的铁锈带,他的家人搬到那里是为了从事某个行业,这行业最终离开了小镇,留下了失业和痛苦。
像许多来自山区的破碎家庭一样,万斯主要是由他的阿公阿嬷抚养长大的。他和生父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小时候在阿公阿嬷的家中和母亲以及母亲各种来回切换的同居男友/短期丈夫组成的家中长大。
阿嬷是这本书中的核心人物。和她那一代的许多祖父母辈一样,阿嬷是维系这个家庭的粘合剂。我很了解阿嬷,因为我家里就有一两个这样的老妇人。我也很了解阿嬷的家族——万斯珍视的、战斗的布兰顿家族。佐治亚州山间有一些这样的“罗宾逊”,他们会快活地打猎、钓鱼,甚至可能会打起来——特别是在有人违反了山里不成文的规矩时。
我也是乡下人,万斯和我有很多共同点。我们的家庭都是劳工阶层——我的父亲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我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而我们的祖父母都是大萧条时期从阿巴拉契亚地区大规模移民到俄亥俄州南部从事工业劳动的人,他的祖父母去了米德尔敦,我的祖父母去了代顿和阿克伦。
最终,成年后我们都离开了我们的根,取得了高等教育学位。他读了耶鲁,我读了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因为神在我们的道路上都安排了一个鼓励努力工作、批判性思维和阅读好书的人。但是,虽然你可以把男孩带出农村,但你永远不能完全把农村带出男孩的心。
《乡下人的悲歌》远不止是口述历史,它对两个陷入困境的地域群体进行重要的审视:阿巴拉契亚和铁锈带。这本书值得我们美国人刻意阅读,认真反思。
同为乡下人,万斯在反思我们的国情和自身背景时,给我留下了很多值得咀嚼的东西。以下是三个初步的收获。
有不少作者已经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工人阶级的焦虑是美国不理智政治环境的核心因素,《乡下人的悲歌》也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触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我更关心的是教会。对于许多年轻一代的福音派基督徒来说,唐纳德·特朗普在老年基督徒中的受欢迎程度既违背了逻辑,也违背了圣经。他的丑恶言语、多段婚姻、轻视女性、对金钱的执着和霸凌的举止,都让人对他是否适合担任国家最高领袖这一职务产生了严重的疑问。然而,众多福音派领袖继续支持他——不管有多少恶劣的丑闻出现在新闻里,21世纪福音派对他的虔诚感觉很像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但那个时代的教会急需改革。我并不想说太多,好想要教导你怎么投票——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好基督徒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我不是要基督徒彼此论断,但我不希望看到教会的领袖们不加批判地支持某个候选人。
我相信万斯的经历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启示。在他的书中,阿嬷经常谈到基督教传统、基督徒责任、神的计划、神的各样恩赐,就像许多福音派一样,然而在下一秒她又像加特林机关炮一样从口里喷出大量f开头的脏字儿来。这就是我们许多南方人在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那种挂名的福音派,一面声称“真爱要等待”,一面在威豹乐队的重金属摇滚中寻找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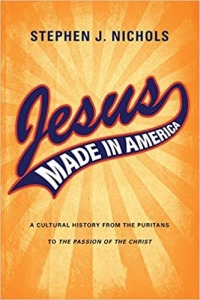 万斯说,阿嬷的宗教里有两个神明:耶稣和国家。但阿嬷相信的更多的是个人主义的耶稣而不是圣经中的耶稣。个人主义的耶稣也就是斯蒂芬·尼科尔斯(Stephen Nichols)在《美国制造的耶稣》(Jesus Made In America)中所说的耶稣:一个感性的个人救主,而不是教会的元首(在阿巴拉契亚的大部分地区,体制性教会并不重要)。这是乡村音乐中的耶稣,是吉恩·维思(Gene Veith)的《乡间福音》(Honky-Tonk Gospel)中的救世主——一个道德主义的治疗性弥赛亚,在焦虑的长椅上泪流满面地等待,在锯木屑小径上徘徊。这是一个只能赐下恩典,却不能改变心灵的耶稣,这是一个竞选活动常常引用的耶稣。
万斯说,阿嬷的宗教里有两个神明:耶稣和国家。但阿嬷相信的更多的是个人主义的耶稣而不是圣经中的耶稣。个人主义的耶稣也就是斯蒂芬·尼科尔斯(Stephen Nichols)在《美国制造的耶稣》(Jesus Made In America)中所说的耶稣:一个感性的个人救主,而不是教会的元首(在阿巴拉契亚的大部分地区,体制性教会并不重要)。这是乡村音乐中的耶稣,是吉恩·维思(Gene Veith)的《乡间福音》(Honky-Tonk Gospel)中的救世主——一个道德主义的治疗性弥赛亚,在焦虑的长椅上泪流满面地等待,在锯木屑小径上徘徊。这是一个只能赐下恩典,却不能改变心灵的耶稣,这是一个竞选活动常常引用的耶稣。
这也许是我的阿巴拉契亚足迹与万斯的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因着神的恩典,我是由爱我的父母抚养长大的,他们的婚姻建立在他们对基督和地方教会的委身之上。我大部分稳定的成年生活都源于在一个没有戏剧性冲突的家庭中成长,父母委身于彼此、三个儿子和地方教会。
许多在阿巴拉契亚长大的人最终会陷入麻痹性的绝望之中,为他们父亲的罪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父亲,就像上百万首西部乡村歌曲所唱到的,爱过之后就离开了。万斯没有陷入绝望,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的阿公阿嬷。
如果我们说万斯克服了惊人的困难从耶鲁大学毕业,那已经很轻描淡写了。他能写下《乡下人的悲歌》,正因为他是个例外。贫穷、暴力(“乡下人就意味着不知道爱和战争之间的区别”)和动荡都在围绕着他的一生,这就好像出生的时候美国的问题挂在你脖子、成为你的一部分一样。
万斯讲述了他身边不正常的家庭是如何滋生绝望的,而绝望又使许多朋友陷入了药物滥用和火山般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
对于许多孩子来说,第一反应是逃跑, 但跑向出口的人们很少选择正确的门。混乱产生更多混乱,不稳定产生更多不稳定,这就是美国乡下人的家庭生活。
是的,对于美国乡下人或者其他类似群体来说,父亲缺席、母亲独自抚养孩子是大多数悲剧的原因。我在佐治亚州农村每天都目睹了这一现实,它对我的大家庭产生了不利影响。
 凡是父亲和母亲在承诺的婚姻中保持共同生活的地方,其他健康的关系往往会发芽。万斯的生父生母虽然关系破裂,但他阿公阿嬷的爱却变成了帮助他超越环境的动力。
凡是父亲和母亲在承诺的婚姻中保持共同生活的地方,其他健康的关系往往会发芽。万斯的生父生母虽然关系破裂,但他阿公阿嬷的爱却变成了帮助他超越环境的动力。
正如《乡下人的悲歌》所揭示的,美国家庭的解体刮起了一股绝望的旋风。这一点在一代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他们来说,个人责任和以工作谋生是陌生的概念。万斯讲述了一位熟人因为不想再早起而辞职,然后在Facebook上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奥巴马的经济政策的故事。正如万斯所说,这就是腐朽选择的果实,也是其他家庭成员所效仿的选择。
万斯承认政府不能解决劳工阶层的问题。他是对的,真正的问题远比缺钱或社会地位低下更深。在本书的最后一页,万斯就像耶稣所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马可福音12:34)的那个文士一样,用一个具有穿透力的问题痛苦地接近了解决方案:“我们是否能下决心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迫使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够与世界互动,而不是在世界面前退缩?”
只有福音才拥有这种力量。
无论你是像我和万斯这样的乡下人,还是你的族谱上装饰着学者的叶子,我们的根本问题仍然植根于创世记第3章,而唯一真正的解决之道能在罗马书第3章中找到。万斯看到了他周围真正的败坏(原文直译):
基督教所描述的堕落世界与我周围的世界相吻合: 在这里,快乐的汽车之旅可能很快就会变成痛苦;在这里,个人的不当行为会波及到一个家庭和一个社区的生活。当我问阿嬷神是否爱我们时,我请她向我保证,我们的信仰仍然可以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有意义。我需要一些更深层的正义保证,一些潜藏在心痛和混乱之下的节奏或韵律。
《乡下人的悲歌》告诉我们,美国南方迫切需要坚强稳固的地方教会。后来,万斯的生父参加了一个传讲圣经真理的教会,这给家庭带来了其他家庭所没有的稳定。
经常参加教会生活的人犯罪率更低,寿命更长,赚钱更多,高中辍学率更低,大学毕业率也比不参加教会的人高。
万斯正确地将阿巴拉契亚的基督教信仰定义为 “深沉的宗教情感,但对真正的教会团体没有任何关联”,这可是不小的问题。
在结尾处,他思考“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否能真正得着改变”。人类政府,无论多么有限和富有同情心,都会在成为救赎手段这件事上失败——历史的垃圾箱里排列着无数的国家见证了这一点。万斯说,“我仍在探寻那几年前已经丢弃了的基督信仰”,我为他祷告,希望他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归根结底,古旧十架是唯一可以发生真正改变和找到持久喜乐的地方。
作为教会领袖,我们至少有四种方法可以回应万斯所描述的灾难。
说起来,《乡下人悲歌》是生硬的,赤裸裸的,并且(读者请注意)充斥着R级语言,但也很难有其他方式写下这样一本书。历史就是生硬的、赤裸裸的,充满了R级的东西,也许很多人的个人故事也同样残酷。万斯写了一本令人耳目一新、残酷诚实的回忆录,这本书解释了很多美国文化中的分裂和绝望,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揭露了我们最深层的需要——通过福音的力量进行内在的转变。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个引人入胜、写得漂亮的关于真理和恩典的寓言。真理揭露了我们国家数百万人鲜为人知、令人震惊的绝望生活;恩典则表明神不受我们的环境限制,他能用弯曲的杖画下漂亮的直线。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illbillies: My Kinsfo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